上观新闻 2024-10-21 12:16:27
作者:陆冠宇 李楚悦

陈康的肚脐左侧有一块微微凸起。皮肤之下,电子吗啡泵正不停运转。依靠一根56 厘米长的导管,药物一路抵达胸椎第11 节,以每昼夜0.048 毫升的速度进入蛛网膜下腔,并最终循环到脑中枢。
在此之前,疼痛是她无法控制的梦魇 。数不清的夜晚,她在黑暗、寂静与眼泪中挨到天亮。战胜了凶险的恶性肿瘤后, 她 被疼痛更为彻底地剥夺,失去生活,不能自理。
“两只脚外面没知觉,里面绞着痛, 24 小时不间断,痛得脚趾揪在一起。”这是陈康与淋巴瘤搏斗过的痕迹。 肿瘤已经稳定,疼痛却依然如影随形。
直至 四 年 后,陈康的身心才感到久违的轻松。
在所有治疗方案都宣告无效后,药物通过电子吗啡泵以更加精准的方式直达她的大脑 ——作用于人体感知疼痛信号的根源。那里已经被细分出 68 个与疼痛密切相关的脑区,相较于传统的疼痛治疗,直接作用于源头的药物更为 有 效。
随着医学技术、疾病认知的不断深入,人类对疼痛的驾驭能力不断突破。但在医生眼中,这些只是迈出了人类与疼痛和平共存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今天是“世界镇痛日”,我们刊发此文,记录与疼痛周旋久矣的医学、医生与患者。
“治不好的病”
双脚的剧痛是和淋巴瘤一起到来的。过去四年, 6 4 岁的陈康被它困在床上。
今年2月,她照例进行半年一次的淋巴瘤复查,血液指标一切正常。但疼痛还在继续。
“淋巴瘤我都没放在心上,脚疼得吃不消,最开始的时候痛到每天掉眼泪。”陈康是个喜欢出门的人,跳广场舞和打牌是她生活中的乐趣。与肿瘤对生命的威胁相比,双脚的疼痛更让她感到绝望。“痛起来真的不想活,但不能跟别人说。”
为了缓解疼痛,她几乎看遍了上海的三甲医院。最初治疗淋巴瘤时, 医生们曾与神经内科的专家一起 为陈康 会诊,但始终没能找出造成疼痛的原因。 激素和营养神经的药物都效果不佳, “ 最后就只能开一些止痛药 ”, 陈康的儿子回忆道。
母亲治疗期间,他加入了一些线上淋巴瘤社群,从中获得了大量知识和信息。但面对疼痛时,同样的路径无法被复制。 “因为它比较复杂,很难明确病因,所以也没有办法针对性地治疗。”脊髓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马尾综合征、副肿瘤综合征…… 这些都是他试图为母亲找出病因时了解到的新名词。
原发病稳定后,陈康依然奔波于不同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疼痛科,还坚持做了两年针灸, 口服了市面上能够针对疼痛治疗的各种药物,但都显效甚微。日复一日地疼痛折磨让她失去希望。
“心里觉得肯定不会好了,自己痛苦,也给家里人带来麻烦。”四年来,生活的半径不断缩小,她变得不再开朗、失去耐心,家庭生活的节奏也被打乱。
“总跑医院辛苦不说,最好的医院和专家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已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看了。”陈康的儿子说。在化疗医生的建议下,他带母亲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疼痛科,把这里当成“最后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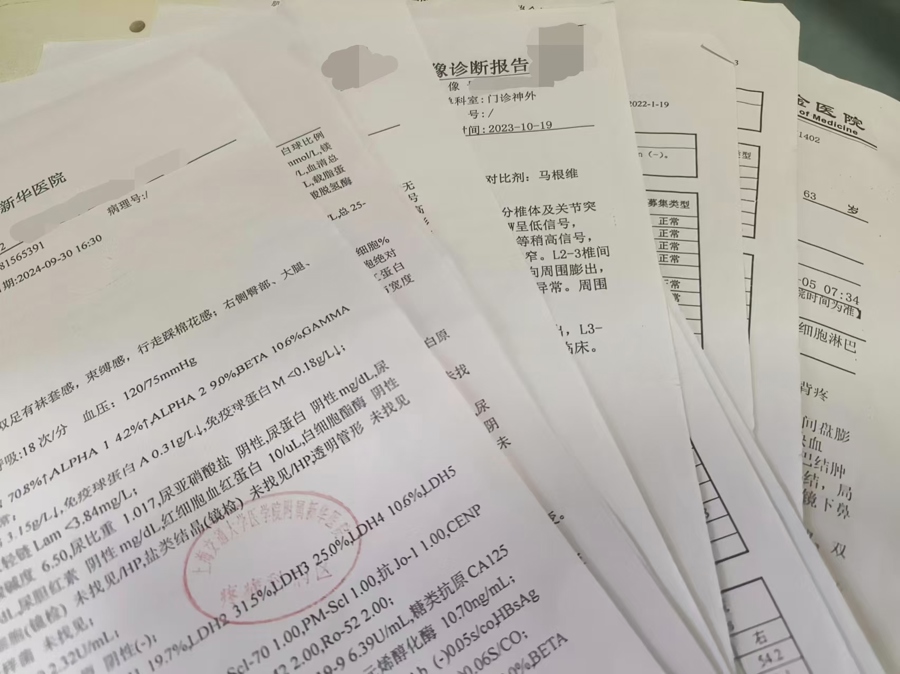
陈康的部分检查报告。 陆冠宇 摄
马柯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疼痛科的主任。对他来说,这种“治不好的病”是工作中经常需要面对的挑战。“正常人服用10毫克吗啡就可以解决问题,有些人服用300毫克还是无法缓解疼痛。”他曾经遇到过一位病情已经稳定的肿瘤患者,却因为日夜不停地疼痛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陈康接受的 “鞘内药物输注系统置入术”已被纳入医保, 惠及了众多遭遇肿瘤疼痛、难治性非肿瘤疼痛的患者。
做完手术后,陈康超过 24 小时没有吃止痛药。在观察期,马柯会根据临床反应,用电子遥控器为她调节吗啡泵输出药物的剂量。术后第十天,她腹部的切口就可以拆线。
想到未来,陈康依然对疼痛的反复和规律不定略显担心。但现在,她可以在搀扶下自己上厕所,也不再需要整夜盯着天花板熬到天亮。
向大脑进军
更多时候,消除疼痛、控制疼痛仍是疼痛科医生始终致力的方向。为了更精准地解决这些 “治不好的病”,医生在 药物治疗之外,还利用最新的科技,向疼痛的源头——大脑,一次次发起进军。
让陈康重拾希望的镇痛泵,通过微创手术埋进她的腹部皮下。不出意外,这个月饼大小的黑色圆盘依靠电力,可以在她的身体里昼夜不停地运转至少 81 个月。
“它是一套全封闭的电子自动给药系统,药物被导管送到蛛网膜下腔,随后 随着脑脊液的扩散抵达大脑。”马柯解释。他判断,是肿瘤造成的感觉神经系统病变导致了陈康的疼痛——虽然淋巴瘤已经稳定,但它造成的痕迹无法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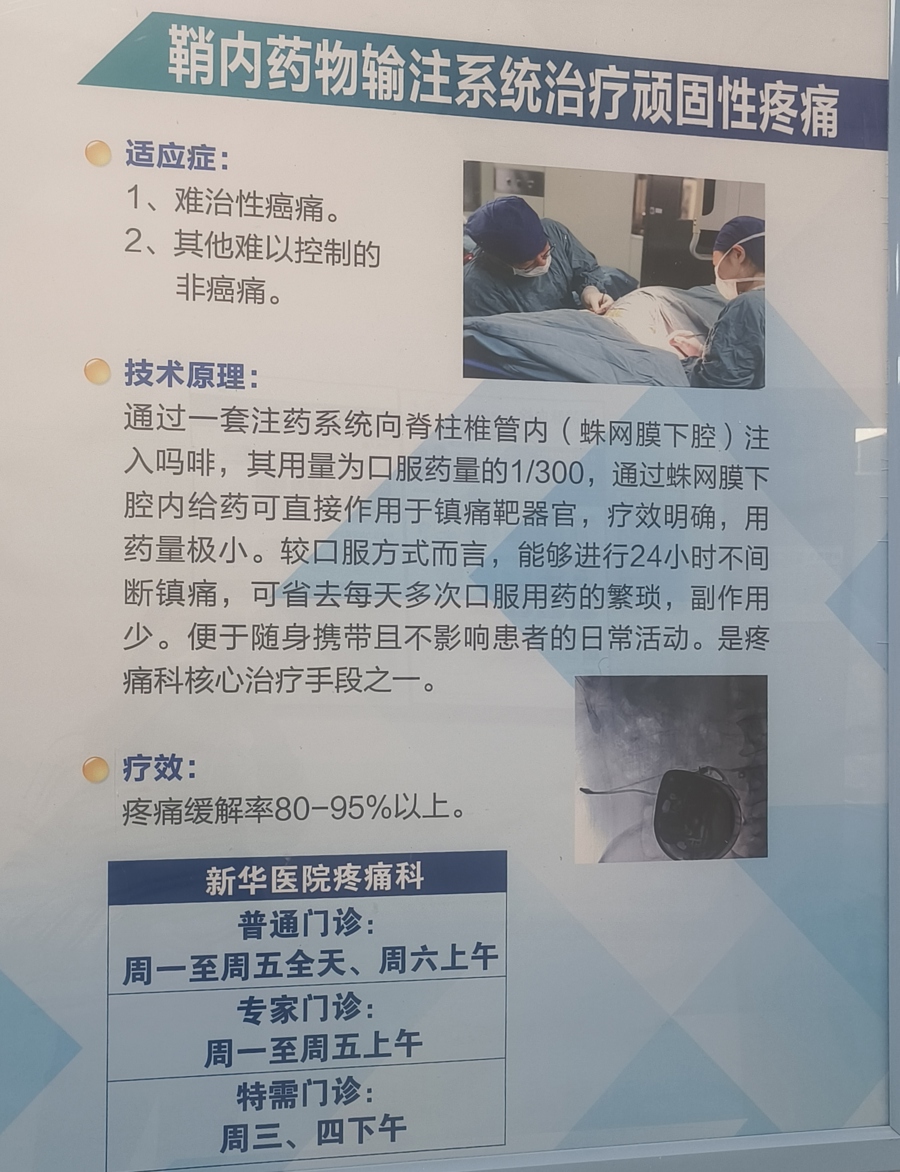
新华医院疼痛科的走廊上,张贴着陈康所做手术的介绍。 陆冠宇 摄
疼痛本身也会带来这样的痕迹。“每一种疼痛都会在大脑留下烙印,我们希望找到能改变疼痛机制的方法。”马柯说。
马柯遇到过很多患者,在疾病痊愈后依然感到疼痛难忍。他与团队临床研究的最新技术是 “无创脑机接口”。通过佩戴 MR ( Mixed Reality ,混合现实)器械,用虚拟的影像、声音、触觉,甚至气味影响大脑皮层,帮助患者建立一个“崭新的自我”,这意味着神经调节与重塑的可能。
“目前它持续镇痛的时间不长,人脑虽然很容易被‘欺骗’,但并不容易被改变。”马柯说。他们试图借助虚拟现实为患者创造一个放松的环境,“像个小橡皮擦,让疼痛的痕迹进一步淡化。”
在 作用于 大脑的 无创技术大规模投入使用前,微创手术是疼痛科常见的治疗手段。
三叉神经痛被称为 “天下第一痛”。过去的治疗方案是“打开脑袋,在神经受压迫的地方垫一个棉片”,即便如此,也依然有复发的可能。而微创技术可以将一根小导管从面部穿入,使用造影剂压迫两三分钟,再全部抽出,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一位曾受三叉神经痛困扰的高龄患者在术后感到奇怪:怎么连个刀口也没有,但确实感觉不疼了。
“根据我们 15 年的随访,它的远期疗效和开刀一样。”马柯说。
疼痛手术的发展是许多医生不断开拓的结果。像三叉神经微创手术这项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治疗技术,在二十多年前,是人类应对疼痛时难以想象的方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是当年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回忆,疼痛界前辈倪家骧教授评价他为“疼痛外科第一人”——疼痛科大夫里第一个把脑子打开的人。
路桂军曾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住了七个月,专门学习如何通过开颅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那是 1997 年,他在病房里见到十来个来自不同省份的三叉神经痛患者。
在济宁进修学成后,他为患者做了一场三个多小时的开颅手术。这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度以为自己是牙疼。做手术前,她的牙已经被拔光,却依然被疼痛折磨得日渐消瘦。 “我遇到了治不好的病,我就想搞清楚怎么回事。”路桂军说。
当时,应对三叉神经痛的主要方法是止痛药和 “射频术”,通过电流产生的热量将神经烧坏,进而阻断疼痛的感知。“损毁神经是用麻木来代替疼痛”,路桂军说,“现在更多的是保留它的功能”。在 2023 年中国镇痛周发布的《我国五区域疼痛领域调研报告》中,“把引起疼痛的神经‘烧’了,就不会疼了”已被列为公众对疼痛的七大误区之一。
从零到一
很长一段时间里, 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是 人类 应对疼痛 的 主要手段 。 虽然能够改善部分疼痛,但是对于很多慢性、顽固性疼痛依然束手无策。
直至疼痛科的出现,疼痛才得到更为细致的分类和诊断,治疗方案也变得更为多元。
在马柯看来,慢性疼痛是一种慢性疾病,可能伴随整个生命周期。其不仅是重要的医疗问题,更是严肃的社会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性疼痛在近15年获得了更多关注。《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有超过 3 亿慢性疼痛患者,这个数字正以每年 1000 万到 2000 万的速度增长。
2007 年,原卫生部将疼痛科纳入一级诊疗科目,明确其主要业务范围为“慢性疼痛的诊断治疗”,并要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开设疼痛门诊。彼时,路桂军所在的邢台市中医院,疼痛门诊已经存在了十年。
20世纪 90 年代,无论医生还是病人,认识疼痛都是“从零到一”的过程。设立疼痛门诊后,路桂军的科室里多了一本书和一张纸,分别是疼痛学家李仲廉的《临床疼痛治疗学》和邢台市的庙会目录清单。
“我们科室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上班,自己给自己讲课,花一年把这本书讲完了。”路桂军说。逢周末赶上庙会,科室就找当地村镇和郊区的卫生所合作,为百姓进行义诊,让更多人知道疼痛和疼痛科是怎么回事。
路桂军是麻醉科医生出身,他知道自己在 为 什么而努力。他举了个例子:就像被蜜蜂蛰到了,麻醉科是给你一颗止痛片,而疼痛科是要拔这根刺,这往前推了一大步。
从基层开始,他三次在不同的医院从零开始建立疼痛科。原来是一厢情愿,后来慢慢开始受到认可和邀请。他自己也在变得越来越专业, “在基层什么疼都看,到了上面关注的领域开始越来越细分。”
马柯有着类似的感受。 “10多年前,我的第一个专家门诊只有一个病人挂号,现在可能要提前一个月才能约到我的门诊。”并非疼痛的病人越来越多,而是更多人开始意识到疼痛科能够在解决疼痛的过程中提供实际帮助。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疼痛列为继体温、呼吸、脉搏、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医学对人的关照不仅仅停留在生存层面,还开始关心生命的质量如何。
马柯的同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疼痛科副主任袁宏杰提到,很多肩周炎患者依靠科学锻炼也能痊愈,但疼痛科通过专业治疗,可以让患者无痛度过疼痛期直至痊愈。他觉得这正是医学的意义所在, “医学的目的是让人活得舒服”。
马柯做疼痛科医生 22 年了,他形容自己经历了“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又是山”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对疼痛相关的医学认知与治疗技术的几番更迭。
今天,疼痛科医生所做的早已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人习以为常的腰椎间盘突出,传统治疗方法中需要开刀,如今已经可以通过微创介入技术来解决,这对许多年轻患者来说,对将来人生的影响也更小。
随着对疼痛的理解不断深入,疼痛科逐渐获得了更为精细化的临床管理策略、临床路径和规范。 镇痛只是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治疗疼痛对患者中枢神经、情绪行为造成的改变,让整个机体恢复正常。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与人工智能有关,医学也同样受益于此。目前,马柯的团队通过 128 个接口,将大脑细分为 68 个与疼痛密切相关的脑区, 并探索如何在不同疼痛疾病中如何针对性地进行无创中枢调节。在他看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精妙的中枢调节,让疼痛不影响患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
“理念必然要先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改变了我们学科的内涵。”认知与技术的发展行至交汇,正带领人类尝试走向应对疼痛的又一个节点。
疼痛难免
时至今日,对疼痛的探索仍未停止。
“疼痛不仅是医疗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它不仅耗费了太多医疗资源,医疗支出也很高。”马柯说。有些带状疱疹的病人找到他时,为缓解疼痛已经花费了 10 万元。马柯觉得,“不是说 10 万块都是冤枉钱, 毕竟有些疾病确实难以在短期内治愈,但让擅长的学科来处理,疼痛科看疼痛病,性价比会更高。”
在技术与认知都有所突破的今天,疼痛科的医生们想要进一步理解疼痛发生时层层叠叠的感受。有时候这种体验不仅关乎躯体,也与情绪和心理相关。而这些细微的差别,有可能正是人类更好地驾驭疼痛的前提。
路桂军曾经得过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他不急着用药,而是先让疼痛在自己身上走一遭。
感受疼痛的部位、做反射试验、分析疼痛范围内的神经…… 作为天天给别人治痛的医生,他觉得自己遭遇疼痛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可以 获得对疼痛更为精准的理解。
再次遇到坐骨神经痛的患者时,他直接问出 “是不是早上穿裤子够不着脚?是不是快走迈不开步?”这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一下就说到病人心里去了”。
这种 “被理解”的时刻并不总是在需要时出现。
“一个看起来健康的年轻人有多痛”, 是林音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疼痛经历时的第一句话。 “看起来健康的意思是,很多人会觉得你年纪轻轻,看起来啥事也没有,但为什么每天都在抱怨?”她曾经因为胸部疼痛去看肺科医生,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年轻不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你不用来了”。
“我觉得 一个人的 疼痛 感知 和 心理状态 有很大 关联 ”,林音说。在不同状态下,她自己对疼痛的理解完全不同。“在我不疼的时候, 也 理解 不了疼 痛 发作 时 的 自己 。 ”疼痛的经历 有时候会 让她 想到 ,人和人之间可能 没办法真正 达到 共情 。
刘涵 也有 类似 的想法 。 因为 常年 痛经 , 她 每次生理期不起床吃饭,都会被母亲指责不够坚强。 “ 我妈 妈 会举她同事痛经打 120 的例子,她觉得那 才是真的痛到不行。 ”
但刘涵觉得疼痛是不能被比较的, “没有人 能 真正感同身受, 不同 个体自身就是最大的变量。 ”
路桂军发现,如果患者不被医生和身边的人理解,产生 关于疼痛的 “信任危机”, 痛 感 就很可能转化成痛苦的状态。
“应对疼痛和痛苦都是疼痛科医生的本职工作”,路桂军 认为, 让疼痛患者免于陷入痛苦,需要一种 “全方位的医学”——先缓解疼痛、恢复尊严,再让患者回归家庭,能照顾自己,也能承担社会角色。从身体到心理到社会,都包含其中。
他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文物修复师:挖到一个破碎的文物,先要把它粘在一起,恢复创伤。然后要恢复它的文化,展示它的纹饰图样。最后让人们知道它属于哪个时代、谁拥有它、它又蕴含哪些故事。
与 原因不明的 关节痛 共存了 二十多年后, 林音 已经把 它 视为 生活 的 一部分。 她看过骨科,查过风湿免疫, “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疼痛又是真实存在的。” 最严重 的 时候, 她 抗拒 出门, 无法 正常社交 , 甚至 怀疑 自己 是不是 得了 骨癌。
在 与 疼痛的 周旋 中 , 林音 开始 逐渐 了解 自己 的身体 , 摸清 疼痛的 “ 脾气 ” , 接受 失控 , 并且 相信 自己 可以把 生活 “ 拉回来 ” 。
她觉得疼痛 是一个 整体性的 问题 , 不疼 并不意味着 解决了 一切 。 “ 这些 经历 会在 人 心里 留下 创伤 , 需要有 更专业 或者 更适合 自己 的 方式 去 治愈 它 , 然后才能 往前看 。 ”
即便是疼痛科医生,也不认为人类能够完全征服疼痛。 “我们会向一些疼痛投降,至少有 5% 的疼痛是我们解决不了。 ”马柯说。但他也指出,哪怕是那5%“难啃的骨头”,医学仍在与之周旋。 人类想直视疼痛、理解它、尝试控制它。这是生而为人共同的困境。
疼痛难免,但医学永不停止。 正如 曾获美国人类学最高奖的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凯博文在《疾痛的故事》的卷首语中写道, 本书旨在“帮助我们认可自己和别人的悲伤。这么做,我们就能锻造出更加公正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 ”
( 应受访者 要求, 陈康、 林音、 刘涵 为 化名 。 )
责编:张德会
一审:宁静
二审:肖秀芬
三审:张德会
来源:上观新闻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