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 2016-02-22 15:4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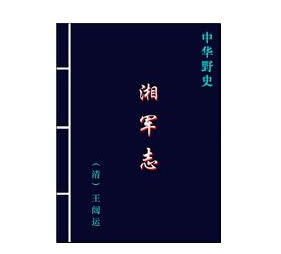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发展壮大的湘军,不仅成为清末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更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除创始人曾国藩外,其他如曾国荃、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个个响当当。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于是,有人发出修《湘军志》的呼声,以免在这批人死后,共同创造的丰功伟绩烟消云散。
找谁写呢?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王闿运。此人乃文坛奇才,曾国藩密友,湘潭举人,对湘军既了解又有感情。曾国荃以高薪把王闿运请来,提供所有文字资料,望其能用如椽大笔将湘军历史做一梳理。王闿运也不推辞,只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初稿,又过三年,最后定稿。
不料曾国荃看完书稿,勃然大怒。该书对湘军诸人不乏贬抑,出资修志的曾国荃更是首当其冲。如,曾国荃围困金陵时,朝廷命李鸿章前来助攻。曾国荃不愿意李鸿章分享自己的胜利果实,便命将士日夜挖掘地道,以期在李鸿章到来之前破城;捐资筹备军饷时,只劝穷人捐钱,却不敢向富贵之家张嘴;湖南藩司李榕倡言大户捐米,曾国荃家有田地百余顷,李榕问都不敢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曾国荃命人烧了根据王闿运书稿制作的模板,又令王定安重新写一本《湘军记》,校正《湘军志》中的一些说法。而王闿运显然很看重这本书,事后自己刻印再版。
王闿运还写过一本《湘潭志》,亦毁誉不一。在这本地方志中,他提到,侍郎陈树棠横行乡里,逼死县官,被巡抚弹劾;本地巨商人周环,据说起家时毒死过一个胡椒客,尽没其资,完成原始积累,虽无证据,王闿运依然提及;再是,王闿运对名臣黎培敬进行了评价,不乏微词。湘潭人常引此三人为自豪,王闿运的一支笔不免掀起了轩然大波。三人的后人纷纷提起诉讼,要求更改。在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最终还是做了修改。因此王氏所作《湘潭志》,有两个不同的印本。
对于王闿运的所作所为,后世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不阿谀媚世,不捧权贵的臭脚。而且王闿运自己也是这样设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明确表示想写一部步《史记》、《后汉书》后尘的《湘军志》,而实际上,这些并不足以保证王闿运写的历史一定可信。态度,是信史的一方面,而掌握材料的多少、分析材料的能力、表述材料的角度、难以完全切除的个人立场等等,都会影响后人的理解。如果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人,有着和司马迁一样的良心,一样的扎实态度,写一本同样内容的《史记》,保不齐若干章节跟司马迁大相径庭。
中国人讲“信史”,向来寄希望于个体作者的良心、见识、文笔等等,这对史家来说压力太大了。曾国荃的做法倒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想尽量立体、全面地反映一个史实,可以多找一些不同立场的人来描述同一事件,提供尽可能多的视角,后人对比理解,自然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若心怀鬼胎,顺我者存,逆我者毁,又另当别论。
>>多读一点
一书激起洞庭波——王闿运与《湘军志》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而湘军正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同光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也相继失败,以农民兄弟的鲜血染红自己官顶的湘军将领也在走向衰亡。他们担心如果不趁一批湘军将领还健在的时候,把湘军的所谓“功劳”“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就可能造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的后果,因而议修湘军志的呼声日渐高涨。光绪元年(1875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
王闿运少负才名,敢为大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在他死后,有人这样评他:“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他的名士习气由此可见一斑。但综观王的一生,却是有才无命,“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在草稿初成之后,王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作入川之游,因而定稿之后也就先在成都刻板。光绪七年十月,王携板回湘。没想到,一番风波正等着他。
王闿运毕竟是文人而非史家,因而在接受纂修《湘军志》的任务后,才真正认识到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凭他的个性,虽然遇此困难,似乎很难中途歇手,而且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展示才学的大好机会。事实也恰恰证明,他在接手纂修《湘军志》时,就很想以自己的才学识来完成一家之言,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湘军志》就是一部颇具个性色彩的史学作品,而非循情应景的泛泛之作。虽然他在书中拘于阶级立场,对太平军等农民斗争极力诋毁,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品格、才略大加赞美,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艰难、挫折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他也直抒胸臆,并不隐瞒;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他更是秉笔直书,痛快淋漓。当然,他这样修史,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曾国荃等湘军将领请他编《湘军志》的目的是要为湘军将领溢美,而不是露丑。果然,在曾国荃等看到王作《湘军志》后,极为恼怒,同声谴责。相传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
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深地感到“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事虽如此,但他始终心有未甘,所以在光绪九年九月重校之后,他又在四川重刻再版。重刻之时,王坦言,“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循情”,因而对于“众人喧哗”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的这种态度在光绪二十三年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说得非常明确,他称自己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
曾国荃等既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品评湘军人物语带讥刺、隐功扬恶甚为不满,又无法禁绝《湘军志》在社会上流传,就只好采取别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补救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曾国荃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二是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
王定安的《湘军记》始作于光绪十三年,完成于光绪十五年,阅时几三载,足迹遍五省。《湘军记》共分二十篇,包括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勘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以体裁论,较《湘军志》要完整。又因为有《湘军志》这个底本,王定安的续作对于《湘军志》的疏漏处自然可以补添完整,因而资料就更为丰富,而叙次也更赡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驳斥《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主要是郭嵩焘兄弟俩。郭氏兄弟在王闿运作《湘军志》前就有纂《楚军纪事本末》的打算,“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现在既不满意于《湘军志》,遂萌改作之意,但终究没有完成。他们对《湘军志》中的疏漏错谬处或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一笺出,加以批评订正,以正视听。但当时并未勒成一书出版,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其侄孙郭振墉才把这些批识文字辑录成轶,并加笺注,以《湘军志评议》为名出版。此书对于读《湘军志》者来说,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湘军志》付梓后,虽然反对者甚众,但赏之者也不乏人。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对《湘军志》深许之。他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他所选辑的《续古文辞类纂》就辑录了《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王闿运于一片责难声中得一援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在致黎庶昌的信中说:“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只是在当时情形下,赏之者毕竟太少了。
(新湖南客户端综合自深圳商报、中国日报网)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