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 2017-02-05 09:2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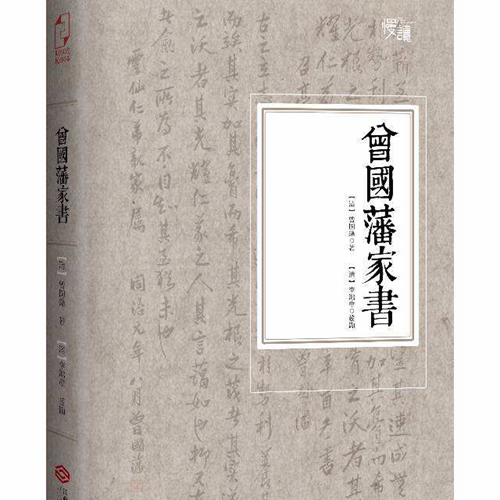
曾国藩后代人才济济,而其他湘军将领为何富不过三代?
文丨肖夜明
春节假期要读一本书。刚好这几天值班时看了不少有关家书、家风的新闻报道,便将书柜里藏了多年的《曾国藩家书》翻出来又看了几章。也许是年龄的增长,读后又多了些小思考。
《曾国藩家书》,是部大家都熟悉的图书,其章节和具体内容就不赘述了。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经过几番改朝换代,其家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家风。曾国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孙辈中,曾广钧23岁即中进士;第四代,曾约农、曾宝荪均是大学校长、教育家;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大都学有所成。曾氏五兄弟,香火延续至今已是第八代。近两百年,可谓无一废人。
然而,再看看那些当年跟着曾国藩出生入死、威震沙场的众多湘军将领,其后人却乏善可陈,鲜有名人大家。我想,这应该就跟我们目前大力提倡的好家风有关。《曾国藩家书》,这样一部书,就是一个家族优良家风的见证和保障。
曾国藩的“豪门”之家,跟他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这部《家书》里,我们看到曾国藩独特而系统的名利观、人生观。曾国藩认为,大富大贵不是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则庶几可以成大器。”曾国藩当大官后,他给家里邮寄的钱反而减少了,他这是不愿自己的后代沾染奢靡之气。“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儿子若肖,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而且,曾国藩认为自己虽然功绩甚伟,但战争中的杀戮屠城、死人无数,实是造孽,非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曾国藩要求后人不要走自己当年的人生道路,尽量远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界、军界。从近些年来的资料可以看出,曾家一脉至今,有突出成就的多达200多人,但基本上集中在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曾家后人,性格上也多“温和,老实,守规矩,不张扬”,更接近“耕读”、“孝友”之家风。
作为一个儒者,曾国藩一生立身行事,纯然是按照《大学》的逻辑架构展开。他的一生,其实只做了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比着来看其他的湘军将领。敢打敢杀、勇猛过人,是他们的标签。他们中虽然也有一些读书人,但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他们一路攻城掠寨,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他们功成名就后,自己忙不迭地尽情享受着荣华富贵,留给子孙后代的,就是金银财宝、阔宅大院。这些悍将猛士,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们的老大曾国藩一样,要给后代留一点精神上、文化上的遗产。更谈不上写出一部像样的家书给后人了。无论在“修身”上,还是在“齐家”上,他们自己一辈子的追求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要求,多停留在物质欲望等较低层次上。富不过三代,这一魔咒,就必然地应验在了他们身上。(肖夜明)
这个话题,我在几年前对湘军故居进行走访时也思考过。因观点有延续性、补充性,特附上当时见报的一篇小文:
——————————————————————————————————————————————————————————————————————————————
从富得流油到家道中落 湘军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听闻涟源仍然能够看到成片的湘军故居,记者近日(2008年7月)随同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一路看将过去,看着看着,就有了些许感慨和想法———
七月的阳光,热辣而具通透力,似乎能让人间的任何秘密无处可匿。但走在山水秀丽的涟源杨家滩一带,望着那一座又一座的清末老宅,兴奋却又迷惑。兴奋的是,此地居然有这么多气势恢弘、保存尚好的湘军故居;迷惑的是,这些富得流油的湘军先人,他们的家为何都在一两代后就中落了呢?他们的钱后来都到哪里去了?
清末的湘军,起源于对太平天国的抵抗和镇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财富转移的方式。这支军队经过无数血战,为当局赢得了一时的安定平稳,同时也掠夺了战争地区的大量财富,把江浙的金钱甚至美女,转移到了湖南。用武力“扶贫”,使当时的湖南顿时成为全国的富省。而在曾国藩的老家周边几县,尤显殷实。
曾国藩选用湘军将领,既重书生士人,又重同乡亲姻。书生士人受过儒说传统教育,知书通经,有理性的忠诚,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同乡亲姻,有共同的乡土情感,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湘军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样,湘军形成了以书生士人为主体,以同乡亲姻为纽带的军事指挥群体,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堪称登峰造极。
曾国藩和罗泽南在杨家滩所选用的李姓名将和刘姓名将,正是这样一批同曾、罗同乡联亲的书生士人。李姓名将有李续宾、李续谊、李续艺、李光久等,刘姓名将有刘腾鸿、刘腾鹤、刘连捷、刘岳昭等。这些人战后不少官封巡抚、总督等职。
“攻南京,发洋财。”杨家滩的百姓,直到今天都还在传说着这样一句话。史料记载,金陵破城后,湘军编制大乱,连各营长夫也都争先恐后参与抢劫,而主帅曾国荃意甚默许。湘军打下金陵,火烧三天三夜(也有说八天八夜,后被一场大雨浇灭),大船大船的财宝,通过水路运回湖南,他们用掠夺来的钱财起屋、买田、娶媳妇。当时湘军将帅纷纷成为豪富,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湖南凭空冒出许多“军功地主”。而湘乡“军功地主”之多,为全省之冠。
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据说“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有种说法,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长期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嘉奖。但湘军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不论有多么样的客观因素,依然是不道德的行为。
其得也快,其失也速。湘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但是,由于当地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都极不充分,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似乎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大多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而是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于是,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因素,流入的财富又大量流失。到了民国时期,湘乡等地依然很穷。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曾遭受惨重破坏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却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
湖南曾经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缺乏产生巨商富贾的土壤。涟源杨家滩周边方圆数十里,据说当时几乎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作坊和实业。湘军从江浙掠夺大笔原始积累后只知道买田置宅,却几乎不应用于商业投资。这或许是当时的湘军不能一直延续富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走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少数湘军在支配这些掠夺来的财富上,还算明智,修路修桥,开田造地,大量地办学校,大量地将湘军子弟送到外国深造,这为第二代湘军人物高起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湖南出去的留学生很快成长为国之栋梁,成为改朝换代的急先锋。这个时期的湘军人物,继承了曾、左、胡湘军人物那种自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思想上已与清末的湘军那一套观念决绝。湘军不再是清廷的保镖,而成为清廷的掘墓人。这个时期的湘军,较之清朝时期的湘军,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另一层意义上的推动作用。(肖夜明)
责编:肖夜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