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火童书会 2018-03-14 09:1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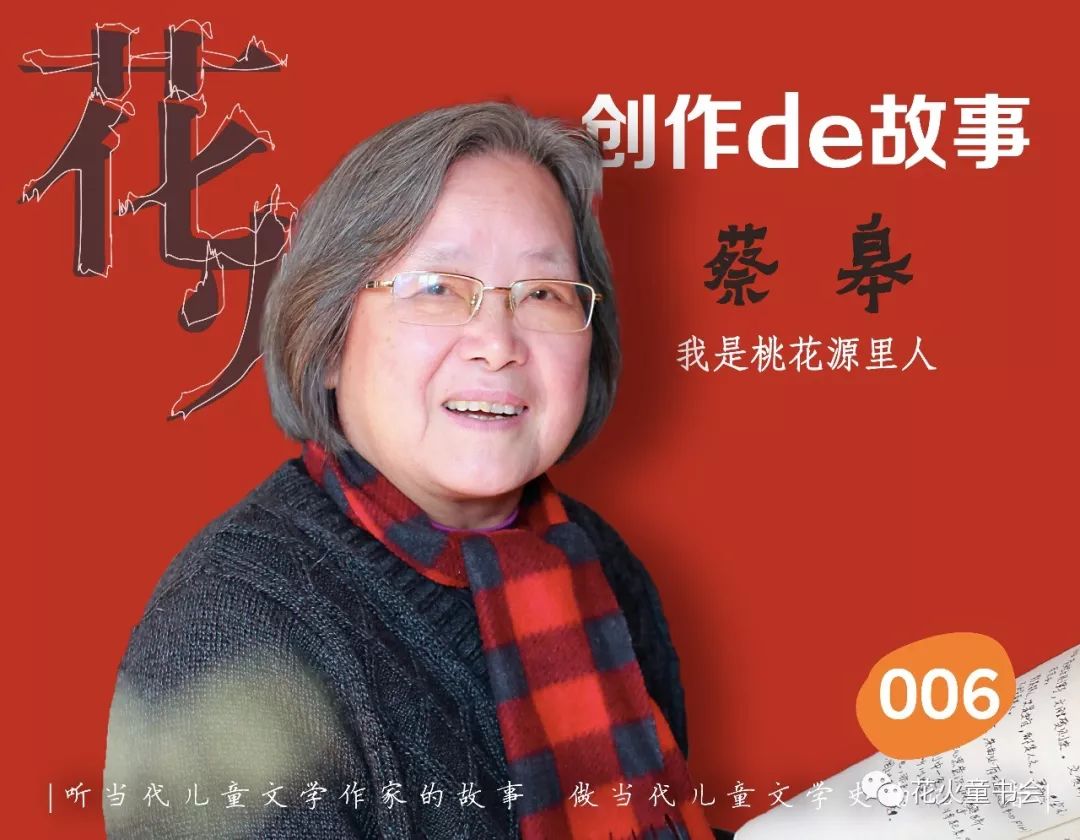
蔡皋:著名绘本画家,生于1946年,湖南长沙人。1982年之前曾在乡村执教13年,之后供职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工作。
获得过「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等奖项,被聘为第34届「波隆那国际儿童图画书插图展」评选委员。工作之余从事绘本创作,创作了《海的女儿》、《李尔王》、《六月六》、《隐形叶子》、《花仙人》、《桃花源的故事》、《荒原狐精》等作品。其中《荒原狐精》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桃花源的故事》原作在日本巡回展出,并由日本福音馆书店出版,次年被定为日本小学国语教材。
听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故事 做当代儿童文学史的记录者

蔡皋老师72岁了。在这个「古来稀」的年纪,她却带着一种近乎「透明」的感觉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双手松松地插在衣兜里,微探着头,门还半掩着呢,笑容就快要溢出来。她满头鹤发,穿一件旧旧的深灰色长毛衣,两片红格子围巾规规矩矩地叠在颈间——像个见着生人有些害羞的孩子,反而用一种不自知的活泼,衬得主人的肤色更加白皙又红润。
此前,我看到的蔡皋老师大多是厚重的,风尘仆仆的。采访者喜欢拍她在顶楼花园里劳作的场景。那时的她,更像一块身披阳光的石头,安心地趴在泥土上,呼吸满园植物的芬芳,欣赏虫鸟鱼蛙的歌唱。
等到镜头慢慢拉远,自然景观的背后开始高楼林立,人们才恍然大悟:哟,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竟然还藏着这样一处野趣盎然的「桃花源」!
透明如孩子,厚重如农人,这便是我心中的蔡皋老师,人们常常在电视里看到的这座顶楼花园,是她的第三个「桃花源」。她就像「桃花源记」里的那位渔夫,穷尽一生去追寻,只为成全自己当一个「桃花源里的人」。
寻找:“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
1946年,蔡皋出生在长沙。
彼时的长沙还是「老长沙」——「老」只是相对现在的时间而言。事实上,那时的长沙像极了一位眉清目秀、温润规正的年轻姑娘,一条街有一条街的故事,一个区有一个区的作用。用蔡皋的话来说,「那时的胡同就是那么长、路就是那么窄,民风也很淳朴,一切都很放心」。
青石巷7号是小蔡皋的家,屋前的小巷留下太多她和小伙伴踢毽子、跳房子的笑声。蔡家是书香门第,祖辈和父辈都是读书人。读书固然为蔡皋的生命埋下了涵养的底色,但回想起来影响她更多的是,「我们家人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很正直、宽容」。
父亲常年在外忙碌,家里由外婆、妈妈和姨妈操持着。小辈一共姐妹六人,蔡皋是老大。不过,她这老大当得很轻松,一方面从小跟在长辈身边耳濡目染,孩子们早已习惯为自己的事情做主,有问题大家再一起分担;另一方面得益于家风宽容,凡事都会鼓励放手去做,长辈们总能从结果中看到好的一面。

年轻时的蔡皋
小蔡皋长到了能领着二妹去上学的年纪,一家人放心让她俩摇摇晃晃地去学校了。但老大嫌麻烦,不爱带伞,一下雨,俩人就得淋着雨奔回家来。外婆不仅没有责骂过她,反而总把表扬备得足足的:打赤脚了?没关系,鞋子没淋湿,「识得艰难,爱惜物品」,真是个好孩子;没打赤脚,把鞋淋湿了?也没关系,「爱惜身体,免得病,省得钱」,孩子,你一样很懂事。
蔡皋的自信在外婆的浇灌下一点一点疯长起来。等到爱上画画,她的胆子更大了,家人的宽容也跟着水涨船高。任凭她用木炭在每一张门后的雪白墙壁上涂鸦,也从来没人批评她半句。邻居齐嫂子更有意思,不仅每天抱着婴儿跟在她身后看得津津有味,有一天,竟然还邀请她去自家墙壁上「作画」,着实把「小画家」给高兴坏了!她大笔一挥,一幅后来被齐嫂子珍视和保存了十多年的作品又诞生了。
家,是蔡皋的第一个「桃花源」。童年的小溪汩汩向前,沿途风光无限。小蔡皋溯溪而行,新鲜温暖的风景次第展开,趣味有了,脚步自然也轻快了。她只顾将快乐、自信、开朗、积极……的小石子儿收入囊中,根本不记得还要去打探路途遥远的事。
等到时间的洪流吞没几十年光阴,童年的小溪依旧庇护着蔡皋,为她注入滋养生命的源头活水,令她扎根在孩子的世界里,为人澄澈如白水,处事稳重如磐石。
发现:“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
友人曾指着「桃花源的故事」里那一页「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问:「在这个明暗对照的关键一处,为什么你只画了个条形洞?」
蔡皋答:「原因只有一个——我不爱钻洞,阴森森的,这不是我要的。」
读书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由白转黑,蔡皋一家因此有过太多阴森森的岁月。狂风暴雨逼得人人匍匐前行,一些根底轻飘的人很快就被吹倒在地,另一些人走着走着就站到了风雨那边,转身将脏水泼给身边的人,毫不掩饰地展露人心之黑暗。
蔡皋向来不爱带伞,她很早就有过在风雨中奔跑的经历,即便如此,风雨打在身上还是冰冷和残酷的。好在她心里清楚家在哪里,到家就好了,那里没有苛责,只有温暖 —— 一种从小就有的方向感,让蔡皋慢慢从绝望中回暖,脚步也不那么沉重了。让一个有定力的人去看风雨,蔡皋说,「你会发现,风是好的,雨是好的,有时,逆成全反而是一种更好的成全」。

19岁,蔡皋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去了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重新分配,她又被分去了太湖乡太湖小学。一开始,她认为农村代表落后,是没有文化的地方,小姑娘觉得自己被「流放」了,每天难过得只想哭。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了乡村的趣味,朴实的生活让乡村在她眼中变得分外美好起来。
太湖小学坐落在一间唐朝寺庙里,院子里有棵六朝松。放眼望去,周围的山峦以寺庙为中心,像莲花似的层层展开,一块福地浑然天成。就是这块小小的莲心之地,让蔡皋的心也安定了下来。
上课时,她自称「麻辣教师」,生怕孩子们讨厌艺术,一心激发他们的兴趣,怎么有趣怎么来,最后惹得同事向她投诉:「你的美术课很好,但孩子们在我的课堂上做你的作业,我就觉得不太好了」。
画画时,她将一切融入画布,画与生活交相映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她慢慢找回那个大胆打开自己的蔡皋,也在和花草的对话中体味生命宏大。这些无意识的积累,日后都成了她创作绘本时最有意义的养分。
「发现」真是一个美妙的词。无论是在风雨中发现方向,还是从成见中发现乐趣,其实都说明人要始终保持一种自我审视、自我唤醒的能力。
太湖小学成了蔡皋的第二个「桃花源」。在这里生活的6年,不仅帮助她走过青年时代一个个幽暗的山洞,更鼓励她努力去发现人生的光明处——当时以为那光明只是裂缝中一缕微弱的光线,如今看来,它早已穿越岁月,弥漫了山川和苍穹。
守护:“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
在太湖小学的6年,蔡皋除了与孩子和自然为伍,也与亲密爱人为伴。来太湖小学的前一年,先生萧沛苍有一次和她同时作画,被她对色彩的敏感所吸引,二人自此识于微时,苦乐相伴,开始共同创作「余生」这件艺术品。
有了孩子以后,蔡皋更忙碌了。前有13年的乡村教师工作,她忙着发现更丰富、更真实的中国民间传统;36岁以后的儿童图书编辑和绘本创作中,她又忙着完成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陪伴两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即使有所体悟,蔡皋也很难及时将它们记下来,回头想想,倍觉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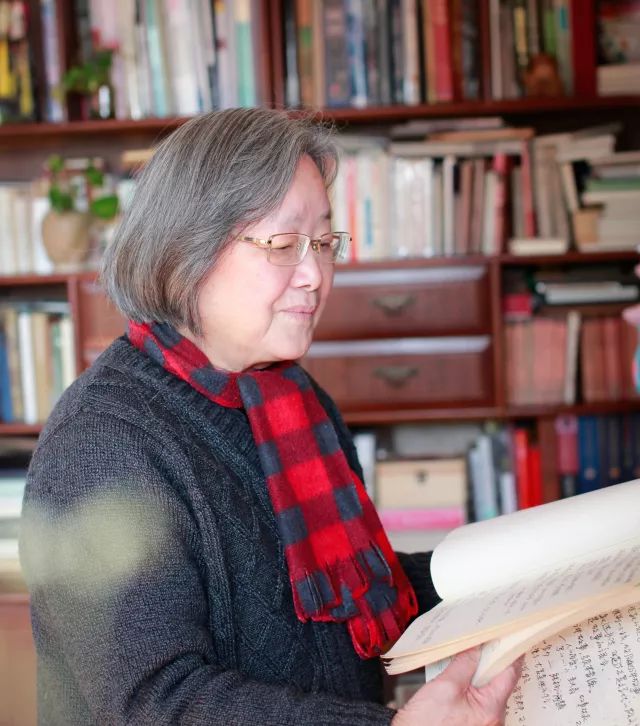
这一课终于在自己退休、孙辈降生之后补上了。蔡皋拿起手边的笔记本,「啪啪」拍了两下封面,告诉我这是「一本微笑的书」,随后她翻开第一页念给我听:「我用手拍打他的背,你是我的宝贝,我说;他用小手拍拍我的背回应我,你是我的宝贝。这个时候,我们俩都觉得非常之安稳」——页面上有二分之一的空白,另外二分之一则用寥寥几笔、简单几句勾勒出一幅小小的祖孙图,以小见大,读之深情,观之静心。
这样的笔记本有很多本,蔡皋美其名曰「我向小孙子学习、和他合作的作品」,孩子成长数年间点滴的天真皆被记于其中。读完一篇还不过瘾,她又把另一篇翻出来:「这是什么?是太极。太极是什么?太极是黑和白的力量。是谁告诉你的?是我自己想的。是在电视里看到的吗?我看过太极拳的。」
回味孩子当初给的惊喜,她显得有些意犹未尽:「啧啧,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停顿几秒后,又再次发出感叹:「我带他一个月,他能给我一个东西我就满足了。可是他每天都有东西给我!不仅是我家的孩子,所有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我的老师。你说,生命、天性可不可敬畏?」
「敬畏」是蔡皋的人生态度之一。这种「敬畏」萌芽自孩提时代她随外婆庄严敬神的经历,生发于青年时期她与乡村自然的日日对话中。
越是幽微细小的事物,越能引发她的敬畏感—— 一张画画的白纸,一朵显微镜下的花儿,一个天真懵懂的孩子 …… 在这些小小的身体里,生命和大自然埋下太多她不知道的秘密,而她的使命是寻找和守护这些秘密,将它们变成自己作品中的「扣子」,等待有心的人们一个一个去解开。

最爱外婆的蔡皋,终于把自己也活成了「长沙好外婆」的样子。
她和孩子们怡然自得地在桃花源里生活着,她更学陶渊明笔下的渔夫「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用手中的画笔沿着来路做下无数的标记,只为带领我们去追寻桃花源,去见天地之大美,去取为人之根本。
真正的桃花源里人,其实就像蔡皋一样,希望天下有心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桃花源。
责编:李婷婷
来源:花火童书会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