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 2018-05-02 16:36:27
文丨记者 文热心 李光华 徐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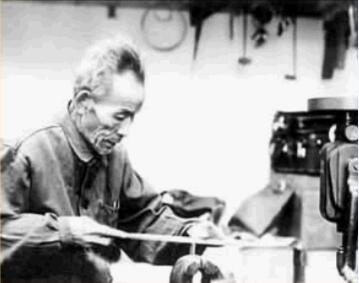
电视剧《枪神》之前在全国热播,里头主人公应德为了八路军官兵能有自己的杀敌利器,竭心研制枪弹,虽九死一生而不悔,演绎了一个革命者“把一切献给党”的忠诚。
只要对历史稍知的人,就可以一眼看出,应德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就是上世纪享誉中外的吴运铎。
吴运铎,不仅是我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而且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在多次负伤、手足伤残、全身留下伤口100余处的情况下,仍然奋斗不息。其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曾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不失其感染力。
吴运铎的事迹不仅感动了中国人,也感动了国际友人。早在抗战时期,史沫特莱参观新四军兵工厂后说:“吴运铎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友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敬意!”1949年冬到1950年春,吴运铎在莫斯科治病时,苏联“保尔”夫人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苏联人民还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
正因为这样,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
“枪神”·雕像
9月10日,记者又一次来到株洲南方航空工业公司科技中心广场,仰望着竖立在这里的吴运铎铜像,追寻着这位闻名遐迩的共产党人在这里的足迹。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决定在南方建一个军工基地。选择的目光朝向这里——已被军管会接管的原国民党十一兵工厂更名为株洲兵工厂。
据长期采访过吴运铎的作者赵长安在《吴运铎传》中记载:1950年5月,吴运铎从苏联治病、学习回来后,没过几天,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指示他:去株洲兵工厂担任第一任厂长。另据南方工业公司史志记载,当年10月,这个厂更名为七一兵工厂,1951年6月再次更名。1951年10月,国家建设航空工业,调整规划,该厂一分为二。留在株洲原地的厂,试产飞机发动机,生产弹药的人员、设备则迁往择址另建的新厂。1952年,那个军工基地的选址最终定在了湘潭,对外称江南机器厂(现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运铎在株洲兵工厂上任后,果断打击了国民党潜伏人员,平息了较乱的局面,稳定了职工队伍,尽快抓好了生产。
吴运铎这座铜像立于2007年10月1日。“南方人”认为,吴运铎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兵工事业者的理想、气节和精神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值得珍藏和大力弘扬。
2
平射炮·枪榴弹
9月18日,记者来到江南公司,见到了吴运铎外甥周宪、周律。他们是吴运铎妹妹吴淑敏的儿子。他们都继承了舅舅的事业,一辈子从事军工,弟弟周律科班出身,干到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哥哥周宪带来了赵长安撰写的《吴运铎传》一书,书中详细地展示了吴运铎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随便选出一“点”,都可让人惊叹: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制成了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威力。” 制造枪榴弹的背景是:1943年初春,罗炳辉师长要求吴运铎研制出一种既能单兵使用,而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新武器。吴运铎目光最后盯在了一篇介绍枪榴弹的300字的短文上,决定研制这种利用步枪发射的小型炮弹。他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和各种迫击炮弹进行研究,最终头脑里有了枪榴弹的设计:把粗钢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弹筒,像装刺刀那样装在步枪口部;用铸铁制成形状像迫击炮弹一样的弹头,装进枪榴弹筒内;再利用去掉弹头的步枪子弹击发后产生的高压气体,把枪榴弹发射出去。吴运铎造出了第一颗枪榴弹,第一次试验也获得初步成功。经过改进的枪榴弹很快装备了部队。1943年8月,日军1000余人来犯,新四军一部在六合县(南京六合区)桂子山与日伪军相遇。新四军当即发射枪榴弹,毙伤敌军300余人,其中日军80多人。战后,新四军将领成钧特地把一支缴获的手枪“奖励”吴运铎。
1944年,为对付敌伪的堡垒,新四军军部决定:生产平射炮弹,并责成吴运铎主持设计和制造工作。吴运铎和战友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仅用4个月左右时间,造出36门平射炮。当这些大炮齐声怒吼,200发炮弹射向敌人,顷刻,密布的碉堡群被夷为片片瓦砾。
罗炳辉师长对吴运铎每一次完成任务都赞誉不已。他曾为吴运铎开过庆功会,隆重地表彰他,赞扬“吴运铎是个宝”,“是一只手将军”。
其实,吴运铎和他的战友们,还建成了我军第一个军械制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8个人的条件下,年产60万发子弹……
3
三次重伤·百余伤口
我们在一栋朴素的宿舍楼里,见到了江南厂老厂长乔世仁。他至今一口大连话,20来岁时被吴运铎招入麾下——大连建新公司实验室。他对这位当时领导他的工程部副部长最新的印象就是“敢冒险”、讲奉献,肯钻研、很聪明。
说副部长“敢冒险”,是因为吴运铎第三次负重伤时,他虽不在现场,却也知道得非常详细。那是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一颗试射炮弹哑火了,等了一会儿仍无反应,吴运铎就要冲上去“看究竟”,人们都劝吴别去,吴却说前线等着炮弹用,我们等不起。吴运铎和吴屏周厂长一起上去。突然,炮弹响了,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医生在为他做手术时没敢用麻药,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但吴运铎硬挺了过来。
《枪神》中有句台词,大意是与枪弹打交道,就是军工人员拿命换取前方的胜利,不冒险岂有作为?试想,那个时候的新四军军工生产不仅要“抬”着工厂与敌人捉迷藏,还要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试枪试炮,更要冒着危险去弄原材料,可谓时时处处与死神相伴。一心扑在枪炮研制中的吴运铎也就多次负伤,留下伤口100余处。因为有了一颗“一切献给党”的心,他不仅顽强地活了过来,而且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
吴运铎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检修土枪实弹射击时,土造枪管突然爆炸,炸伤了左手。可这只不过是负伤经历的“小恙”,后来的三次重伤让他的生命之火差点熄灭。
第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伤口发炎感染,发高烧40多度。医生只得挖去他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
说吴运铎讲奉献,人们都知道,他第一次负伤后,在医院养伤时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说,由于武器缺乏,有的战士还在使用鸟枪打仗;每个战士一般只有3发子弹,平时为壮声势用高粱秆把子弹袋撑起来;打完仗还要把弹壳捡回来上缴以重新装药。他再也躺不住了,拖着伤残的身体、拄着树棍回到工厂。第二次负伤后,他不能下地,就在床上画武器的设计草图,导致伤口迸裂,鲜血直流,但他浑然不觉。医生只好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第三次负重伤后,他在病床上利用尚存的微弱视力,坚持把引信的设计搞完,并让人买来了化学药品和仪器,在疗养室里办起了炸药实验室,制造出新型的高级炸药。
说吴运铎肯钻研、很聪明,乔世仁印象最深刻。乔世仁加盟军工前,在一个日本人钢厂做绘图员,弄了一部近两寸厚的日文技术书。这部书被吴运铎借走。没多久,吴运铎给大家讲课,让乔世仁吃惊的是,吴讲的竟然全是那书的内容。一个“土八路”还懂日文?原来,吴运铎的日文是跟一个日本俘虏兵学的。周宪告诉记者,吴运铎在苏联治了几个月病,回来后可以看俄文书报。
4
一本书·几代人
《枪神》只演绎吴运铎生命之花在抗战中绚丽开放的一段,其实后来他的人生有着更多的精彩篇章。
当然,“后”是“前”的继续,是“前”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前”的抽象和提升。
早在第三次负伤时,吴运铎就说:“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
虽然专业宣传者没有当成,但其“业余”宣传的功效如此巨大,可能连自己也可能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出名了,195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而真正让他“天下知”的,还是那部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在领导军工之余,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这部书。全书分为童年、劳动的开端……我们的工厂、入党……第二次负伤、新任务、制造枪榴弹、拆定时炸弹、我们的平射炮、第三次负伤、永远前进15个章节。这本书于1953年7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后,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书中充满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读者。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印刷,印数达200万册。10年间陆续几十次印刷,总印数达500多万册,还被翻译成俄、德、英、蒙、日、朝鲜六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当时——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都开展了学习吴运铎活动,有的工厂、学校还组织了“吴运铎小组”、“吴运铎班”、“保尔班”等等,开展劳动、学习竞赛。青年们把这部书当成生活教科书。这是一个经历者在本世纪的回忆:双峰一中将初15班正式命名为“吴运铎班”,给全班55名同学每人发了一本《把一切献给党》。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同学们把“学习吴运铎,刻苦钻研,学好本领,把一切献给党”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在这种氛围中,初15班“不仅文化成绩在全年级八个班中数一数二,体育、歌咏、舞蹈比赛成绩也在全校名列前茅”。本世纪“结算”,“吴运铎班”出了2名教授、6名高级工程师,还有更多的各个行业骨干。
上个世纪60年代,《把一切献给党》是雷锋生前最喜欢读的两本书之一,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把一切献给党》。雷锋说,保尔和吴运铎是每个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自己要像他们那样去做。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邓朴方说,自己“深受吴运铎事迹的感染”。
1983年,张海迪(现任中国残联主席)在见到吴运铎时说:“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您,是您的《把一切献给党》那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最初,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不中用了。后来,看了您写的书,心想,您老受了伤,几经磨难,还继续战斗,又搞创作,使我非常感动。” 可以说,吴运铎的拼搏、乐观精神也激励着张海迪这一代人做真正的强者。
今天,有人对这部书发表读后感:“吴运铎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高度残疾的一个人了……然而,为了教育更多的人,他倒在病床上,用质朴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和抉择。”“读来不能不让人思考,活着是为了谁?自从跟了党,他就从没有和党谈什么条件……他追随了党一生,把自己的生命真的完全的献给了党的事业……是什么力量使吴运铎这样坚定不移?是信仰,一定是信仰……”
5
“江南情结”·三位亲人
出名后的吴运铎在哪?虽然做了中南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他人还在湖南,筹建几个军工新厂。
后来,吴运铎虽然离开了湖南,但他的心还在湖南,因为他的湖南缘份不浅。周宪告诉记者,祖籍武汉的吴运铎在萍乡煤矿做机电工人时,那里的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一个洞子里做事,一个锅里吃饭,相交相知很深,就连生活习惯也“湖南化”了,吃菜也是“怕不辣”。日军攻打萍乡时,他的母亲和妹妹逃难来到湘潭十八总,也就是现在韶山、银田、楠竹山一带,而且在这里“吃百家饭”有好长时间。当时,吴运铎已“东进”参加新四军,听到这一切后,心情非常沉重,同时也记住了湖南湘潭十八总。
他领导的厂一分为二后一个要“搬家”,新址最终确定在现在江南公司这个地方,虽然是顺势而为——这里有原国民政府的一个煤矿,解决了燃料问题;这里也有一个小兵工厂,有着军工基础,还有地形地貌等优良条件,却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安排,让他产生了“江南情结”,一辈子也割舍不下这种情结。江南厂建成后,他虽然不再在这里工作了,却把母亲和大哥吴运钧、妹妹吴淑敏安置在这里,大哥和妹妹也就成为江南厂的职工。他的母亲在这里一居28年,最终和吴运铎的大哥、妹妹长眠在这里。
他人在北京,却心挂江南。周宪记得,每次去看望舅舅,吴运铎就问“江南厂怎么样?又上了什么新产品?某某技术改进没有?”那神情,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问多了,周宪就奇怪舅舅为什么这么关心。吴运铎就告诉他:“江南厂的地址是我选的,是否适合建厂是我带人勘测的,设备、人员是我安排的。你说我能不关心吗?”
周宪告诉记者,吴运铎的“江南情结”内涵是丰富的,除了上面两个因素外,还有对这块土地的挚爱。吴运铎后来多次和江南的亲人提起选址、建厂时的趣事,开心得像个孩子。他说:“当时没有电,我们晚上打着手电筒去抓泥鳅、黄鳝,以改善生活。有时候,随便就可以捉到甲鱼和乌龟。”周宪还说一件生活趣事,他上北京看舅舅带的是凉薯、紫油姜。因为舅舅和他聊起江南时,对那一带的特产津津乐道:“我走南闯北,只有湘潭的凉薯最好,既可做菜,又可当水果,又甜又脆,别的地方的硬不是这个味。”于是,带凉薯进京也就成了周氏兄弟的“常规动作”。如果说吴运铎对湘潭物产是出于偏爱的话,那么对于这片土地上出的人物却是崇敬。他说,这片土地了不得,出了毛主席、彭总等一批伟人,还出了齐白石这样的画坛宗师,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吴运铎很佩服齐白石,闲暇时学习齐氏技法,对画蟹更有心得。周宪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时,本来舅舅没有受到冲击,可他对这种混乱看不惯,就画了一幅蟹,上书“看你横行到几时”作为大字报贴了出去,结果被造反派抓住,陷入厄运。他是“自己跳出来的”,周宪笑着说。
江南公司董事长齐振伟告诉记者,其实,不仅吴运铎有“江南情结”,江南人也有“吴运铎情结”。这两种情结是一种精神财富,已融于“江南文化”中。
吴运铎的“江南情结”之所以非常深,深过他工作过的其他地方,除了江南厂是他的“孩子”,还缘于血浓于水的亲情,更有对这片土地的敬仰。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日报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