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2-09-25 00:1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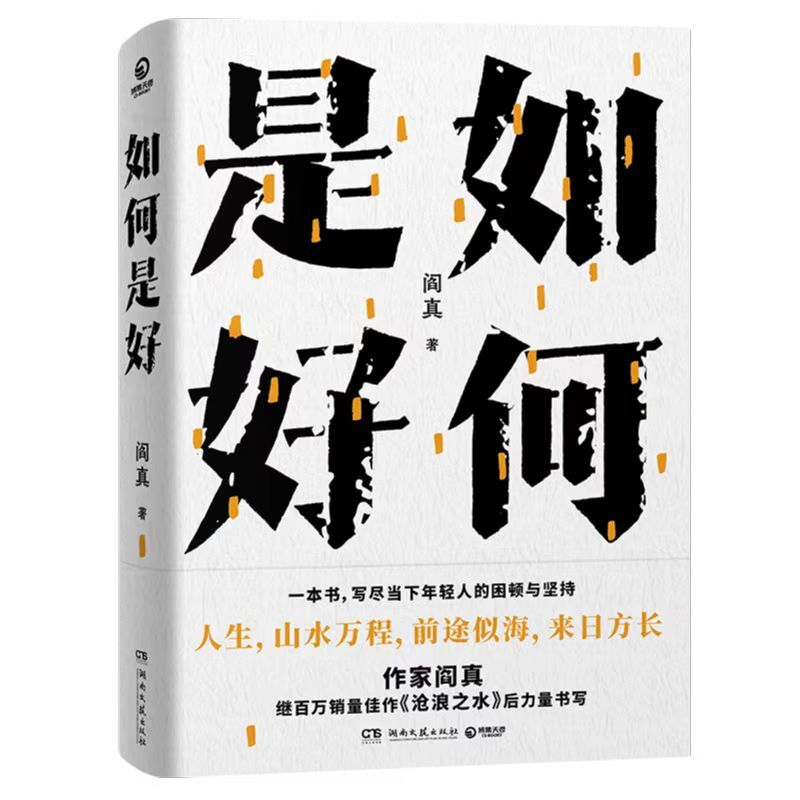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近日,著名作家阎真的长篇新作《如何是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并于9月24日在长沙举办首发式。这是阎真自《活着之上》后,时隔8年潜心打造的又一部全新力作。
1996年,阎真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因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深度探讨而引发关注。几年后,《沧浪之水》成为无数读者认识人生、理解人生的“必读之书”,也成为阎真的代表作。
此次出版的《如何是好》是阎真三十余年创作生涯里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被称为“《沧浪之水》的姊妹篇”。小说主人公许晶晶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优异的大学,拥有了理想中的爱情,并期待着美好的未来。谁知,不但在保研的过程中遭遇“陷阱”,在后来的爱情与求职路上也挫折不断。
在书中,阎真延续着他对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幽微体察,以极为现实主义的笔锋再现了当代年轻人,特别是被现实消解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与尊严之间的对抗。在《沧浪之水》出版二十余年之际,阎真也通过《如何是好》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互文和关照,面对当下,对他始终关注的知识分子困境的主题进行了升华。
在首发式上,阎真还与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一起,就文学能否对抗现实,知识是否真的能改变命运,生存与尊严要怎样和解等话题,开启了一场对话。
对谈摘录丨仰望真正的星空,是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阎真:我写小说是非常认真的,是生命层次的认真态度。我写这本书之前已经积累了一些生活感触,但是方向还不明确。有一件事使我明确了创作方向,就是我儿子研究生毕业以后到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去工作,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有一个月工作了290个小时,每天10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老板还找他谈话,怎么别人工作了300个小时以上,你只工作290个小时?290个小时差不多是法定工作量的一倍,老板还认为没有完成足够的工作量,他就从那个公司辞职了,但是这条路确实很难走。
我这本书是写的没有很好家庭背景的女生,她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人帮助她。她又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我写小说的特点是贴地而行,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就怎么写,这本小说也是用这种生活态度去描写的,表达了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生存发展的困境或者前进的艰难。这是我写小说最基本的动机。
自由是沉重的,所以才会问“如何是好”
主持人(马婉琳):梁永安教授是特别关注青年群体的学者,在B站上特别火。刚才听了阎老师分享的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故事,还有阎真老师对青年人的想法,您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梁永安:第一点,这本书书名没有很大的确定性,正好是今天青年的状态。我觉得它重点还不是现在时,而是未来时。什么叫青年?前面还有很长时间。未来到底该怎么生活?以前的人十五六岁就结婚了,早就被定格了,生活没有“如何是好”的问题。被指定的生活看起来轻松,但整体上很沉重、封闭。
我读《如何是好》的时候,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种幸福。这代年轻人终于有这个问题了,要自己选择、自己判断、自己体会,这是因为我们非常有生机、有生命力。就怕年轻人不问“如何是好”,觉得什么都有,生活是一种定格。自由是很沉重的,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第二点,这本书的现实主义是很彻底的。书里的这个年轻人是上了重点本科的,她处在现代教育比较精华的一部分。这种教育、历史、社会的发展给人提供了一些意识,让人不得不承受生活,但内心深处(对生活)是有距离的。我读阎真老师的书的时候,急着看结尾,到最后她到底怎么安放自己——她自己的价值、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
阎老师其实是在看一个命运。一个年轻人要善于“清场”,面对复杂,自己内心深处要简单。我觉得这本书应对了当下青年精神深处的自我矛盾和诉求。
主持人(马婉琳):我们的理想照进现实应该怎么样平衡?阎真老师写过关于年轻人进入体制内的《沧浪之水》,两本书中呈现的年轻人的状态,或者说两个时代的年轻人的面貌,您觉得有什么异同呢?
阎真:21年前我写了《沧浪之水》,也是一个长篇小说,它的主题是成长,今年写的《如何是好》的主题也是成长,所以有的人把它形容为女版《沧浪之水》。在成长这点上,它是有共同性的,但成功的背景不一样。《沧浪之水》的池大为毕竟还有一个生存的基地,再怎么样只是在机关的发展受到了压抑,条条框框的社会结构要对“我”进行强制性的改造,是不是服从强制性的改造?有这样一种选择。这本小说,我主要是写没有最基础性的生存基地。主人公是重点大学毕业的,走到社会上你能说你算啥?我每年都上大学生的新生课,我就跟学生说这样一句话,“你们能够进到中南大学这样一个985大学已经是百里挑一了,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进了保险箱,你们离那个保险箱还差得远得远得远,也许对你们中间最大多数人来说,你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考上中南大学了,人生最高光时刻已经是过去了,未来式还要靠你们自己的创造,你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成功。”这个话说得有点打击人,但是我认为我还是说出了一个比较沉重和严峻的现实,事实就是如此。
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女性,她有很多想法,首先她要有一个好的生活基础,条件,稳定一点的工作,女生希望工作稳定一点,又想要收入好一点,又想找一个满意一点的男朋友,还想活得有尊严。一个大学生哪一点可以放弃?难道我不要尊严吗?难道我不要好一点的工作吗?难道我不要男朋友吗?什么都想要,但是她认为自己又什么都没有。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要跟这个世界发生有机的动态联系,你要有交流性或者是交换性,总要为社会或者周边人奉献点什么,你才可以得到想要的回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想要,所以中间就非常痛苦。
我小说里也用了一个比喻,“我就像一个又饥又渴的人站在苹果树下,轻轻一跳就可以摘到红叶诱人的苹果,跳还是不跳,不知如何是好。”一跳什么都有了,甚至人家还可以给你婚姻。跳还是不跳,这个苹果摘还是不摘,机会已经在跟前了,不知如何是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生活中的很多选择的确是非常痛苦的,我这个小说就是写出这种状态。
年轻人必须要有“熬”的力量
主持人(马婉琳):面临诱惑,面临困难,面临理想跟现实这种困境,究竟应该如何去选择?梁教授,您跟年轻群体打交道很多,现在年轻人是什么都想要,但现实肯定不会什么都给你,面临这种状态应该怎么去做?
梁永安:年轻人必须要有“熬”的力量,走过去之后是又意想不到的收获。现实是一条更难的路,一个普通女孩子面对这个精彩的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样?其实这个人生哲学过程可能很有价值,体验形形色色。跟上一代或者过早定下来的人比较起来,她的生命体验就拓展了一下,打开了这个世界本质的本象的(东西)。实际上,作为一个弱者,弱者有弱者的生存,这里面有一种生命的新认识。
今天很多的普遍女孩子、普通男孩子都是“搬山”,每一天搬掉一点,过了这个历程,一下子就自信了,对世界、对生命、对自我。
我看这个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后面萤火虫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命的一种新的萌芽。
阎真:你说到萤火虫,我补充一句,我本来根本没有想到萤火虫,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一个什么县发展出了萤火虫经济,大家都去旅游都去看萤火虫,我突然受了启发,把萤火虫写在结尾,跟这个星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画面感,我觉得非常好。
梁永安:特别亲切,因为我有这个体验,我小时候晚上走夜路,特别紧张。但旁边有小树,有萤火虫一闪一闪的,我一下子觉得有了依靠。我觉得年轻就是这样,社会学说一个青年一开始就处在角落里,是看不见的。但身边有个小萤火虫,是心里边那个小希望。
主持人(马婉琳):是的,梁永安教授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写了很长的阅后感,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黑暗中无所不可为,提灯者总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阎老师如何看待这句话呢?
阎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对,那几年关键期最后就成长起来了,其实我也有很强的感受。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在路上的艰难,你把它跃过去了,很多人眼前一片茫然,算了算了,找个人就结婚或者什么样,当然找个人结婚也不是不对,结了婚也还是可以努力,但又觉得实在是太难了,周边这么多聪明人,想来想去就放弃了,结果自己这一辈子就没有什么出彩的机会了。但是艰难熬过来的时候是人生走向胜利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你在淘汰别人的过程,别人不能熬,你能熬,说起来也是有点(残酷),其实我不想用淘汰这两个字,但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
成熟和成长、妥协实际上是一回事
主持人(马婉琳):在主人公面临情感上选择的时候,一开始想找好看的,找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最好能关心人,温暖一点的,到最后她只选择了其中一点,改变了择偶标准,您觉得这种改变是对生活的妥协,还是自己的成熟和成长?
阎真:一方面是妥协,成熟和成长、妥协实际上是一回事。一个女孩子读大学的时候肯定想找一个帅哥,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找一个有才华的,又能够感情专一、对自己很温暖的等等,但是要在现实中实现这些还是相当有难度的,除非你非常优秀。男性也是如此。这既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但生活不是为你而设计的。
我这个小说主人公的选择,不一定有充分的情感,开过她情感这扇张门的男性有七八个。有些是她想要要不到,有些是她不想要的,她自己家庭背景受了局限。
一个男孩子老是想问一下父母有没有退休金?一句话把她问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父母是没有退休金的,她没有勇气面对这个事情,但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甚至不算很高的要求。她有什么勇气去面对这个情感呢?最后她找了一个跟自己家庭背景差不多的。带来了什么问题?生存压力非常大。
举个例子,他们出去买家具,中午不舍得吃饭,买几个包子就吃了,把家具搬回去,又被运输的人敲诈了几十块钱,她心里很心痛,她就说以后我们出去吃馒头,包子都舍不得吃了,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生活化,比较好的文学语言,能够表达这种心态和处境。
主持人(马婉琳):梁教授,您觉得呢?
梁永安:男女性差别很大,活在一个世界上看到的世界不一样的,女性感受的细腻度,她生活的密度比男生密太多,心事也是。比如男性看一个女生,到底是爱她还是喜欢她,男生60%-70%都搞不清楚。女性分辨得很清楚,所以面对一个世界的时候,女性在一生中都是不妥协的,始终怀着一种梦想。人类生活里,情感是女性的主场,她在这个主场里永远不会退缩,这个时候也带来生活里非常强的压抑。人类的生活,文明形态,婚姻制度等等,其实不太适合女生。
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在非常有限的历史情景下看男女怎么相处,婚姻、爱情都是因地制宜的,根据当时生存的内在结构和变化。
生活对女性的挑战还要更加严峻一点
主持人(马婉琳):我很好奇,因为我看这个书的时候一开始是代入男性的角色去看的,看了两页之后才发现是女性的主人公,怎么想到从女性的角度去写这本小说呢?
阎真:其实男性、女性主人公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一个女性,可能前面四部小说有三部是男性,一部是女性,第五部稍微平衡一下,选择了女性的主人公。而且我也认识到生活对女性的挑战还要更加严峻一点,我就是想写出这种生活挑战的严峻性,我是从生活的痛感中寻找创作的动机。如果这个事情非常幸福、非常顺利,那写啥呢?好的小说都是写带有悲剧意味的,因为生活痛感带来悲剧意味。
抛开这些因素都不说,为什么女性的压力大一点?或者生活对她们更严峻一点呢?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她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她们要生孩子,一个男生四十多岁生孩子不是一个问题,对一个女生来说就是问题了,这个时间、空间长度,至少在这一点上她还是比男生承受更大的压力。
主持人(马婉琳):我也很好奇,从一个男作者的角度怎么把女性的那种心理描写得那么细腻?是有做这种调查工作吗?
阎真:我确实写得比较细腻,关于人的心态,我当时是受了别的小说影响,从《安娜·卡列妮娜》小说中受到了启发,但最多的启发还不是托勒斯泰,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我看了他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还看过他的《一个女人一生的24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把女性的心理写得非常细腻,我反复看这些小说。我想了想,虽然我不能在生活中那么恰当地去理解女性,但我可以参照这些男作家的理解。他们理解的程度、深度,对女性的总体情感以及各方面的把握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没有照他们的笔触去写,那我就变成了抄袭,他们写得很精彩的情节,我肯定是不能写的,但我也有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多多少少有一点自己的感触和小小的创造性。
看到星空是对生活一种哲学性的理解
主持人(马婉琳):《如何是好》整本书都写特别现实,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主角无论职场还是感情都面对着无数次生存和自尊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但是无论是信还是书都以星空结尾。星空在这本书里象征了哪些理想和意义呢?
阎真:我为什么爱上文学?我对时间还是有点敏感。时间没有什么意义的,敏感也好,不敏感也好,只有几十年,不能因为你对时间和空间敏感,你的寿命就特别长,可以多活两百岁,没有这个问题。你看着一颗星星,其实那个光是每秒三十万公里,你看到的这个星星已经走了一百年,而不是现在发过来的光。地球在宇宙之中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存在。
看到星空是对生活一种哲学性的理解。你理解了时间和空间之后,就和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什么?意识到自己渺小,瞬间的存在。话说回来,这种认识也没有什么意义,你认识了也好,不认识也好,每天都要活在很世俗的空间里,这种认识不过是你具有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存在。我写了五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尾都有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这成为了我心理上的一个焦点,我每一部小说都是这样的。
主持人(马婉琳):在宏大的时间和空间下,每个人都显得很渺小,像阎老师和梁老师今天说到的,只要每个人都发出萤火虫般的光芒,也能够点亮这个世界。
梁永安:热爱大地,自由生活。为什么?因为大地什么都有,有沙漠、有冰川、有海洋、有稻田,这个世界就是要热爱,你要走过,要体会。我觉得生命的维度最重要的是内在的尺度,所以这个尺度是自由,不是占有,是内心的成长,生命的打开。
阎真:希望年轻朋友至少在大学期间要找到适合个人的、有兴趣的、愿意努力的人生方向,然后为之持之以恒10年、20年。我还希望年轻朋友一辈子一定要找到一次机会,到没有尘埃遮挡的高山或者西北的大沙漠里去仰望一下真正的星空和银河,这也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使命。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