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3-07-04 17:18:06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7月3日讯(记者 廖慧文)7月2日上午,由深圳出版社出版的湖南诗人胡金华作品《雪落在南方的乡下》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暨分享会。
“仰望星空/风会带给你大地的消息”“每当夜深人静/我和柚子树都会流泪”……《雪落在南方的乡下》是诗人胡金华用心浇灌的“一朵小花”,收录了诗人创作的百余首诗歌。全书分为“讴歌时代”“怀念故乡”“思念亲人”“山水游记”“怀旧砭时”五大主题。胡金华笔下的诗歌,或因征文而作,或为感想而发,风格迥异,随心随性。
《雪落在南方的乡下》不仅仅是一部诗歌集,它还是一部记录和表达交相辉映的作品,它记录着时代的变迁,用诗歌独特的体裁,记录着时代、乡村的变化,记录祖国的盛事,记录人间百态。

嘉宾对谈
做一名诗人一直是梦想,胡金华提到,早在1978年那个冬天的阅览室里,他当诗人的梦想就悄悄诞生了。偶然的一本书,一次意外的阅读,一首随性而发的长诗,成为少年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历。几十年如一日的喜爱,观壮丽山河的感慨,睹华夏盛世的继往开来,感家乡的变化和亲人不再的沧桑,这些情感和经历磨练着诗人,让他从过去走到现在,也让他的梦想重新焕发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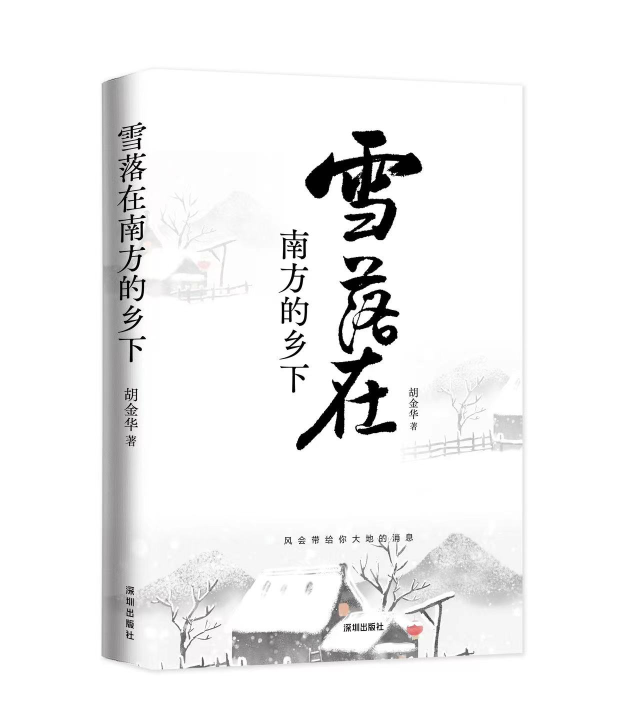
书影
在首发活动中,作者与深圳出版社常务副社长胡钟坚就书中的诗歌创作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深圳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兼深圳出版社社长聂雄前对本诗集评价道:“乡土中国最后的风景已然出现,古老的农业文明因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而行将崩溃。‘最后的乡村’这一无形的悲剧氛围造就了一位真正的乡村诗人胡金华。”
“胡金华在当代诗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读他的组诗《雪落江南》《回乡偶成》和其他一些短章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高尔基对叶赛宁的评价: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人——比天下万物——更配领受)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
推荐语:
乡土中国最后的风景已然出现,古老的农业文明因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而行将崩溃。“最后的乡村”这一无形的悲剧氛围造就了一位真正的乡村诗人胡金华。他以甜润的歌喉咏唱着属于这最后乡村的美丽忧伤和淡漠希望,发自至情至性的诗句表达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切了解和对普通人命运的无限关注。
胡金华在当代诗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读他的组诗《雪落江南》《回乡偶成》和其他一些短章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高尔基对叶赛宁的评价: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人——比天下万物——更配领受)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
——聂雄前
序
诗人自有诗人的爱
李训喜
与金华相识源于他在湖南省怀化市水利局局长任上,那时只知道他是工作狂,为水利的事敢于豁出命去,但不知道他曾写过诗,还藏着一个诗人梦。这两年我兼任水利作协主席,才注意到金华的诗歌创作,眼前不觉一亮,心里也感慨万千。打电话给他,他说退居二线了,可以重新拾笔写些东西。正如他说的:“心底的文学梦从未泯灭,再忙也一直在偷偷地读诗,偶尔还偷偷地写诗。”金华对诗歌自有他的看法,对创作也有自我追求。他袒露自己读诗写诗三原则:一是说人话,要让更多的人读得懂,要让读者知道你想说什么;二是动真情,他反感有些诗人的造作,更反感现实中“从炊烟里走出要断炊烟”的人;三是要有诗意,努力写得有韵味和画面感。说实话,我与金华对诗歌的认识、鉴赏和创作并不完全一致,创作风格也有所不同,但我们内心都有一份对诗歌的挚爱,正是这份爱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也能够相互砥砺、切磋提高。
诗人的爱深深植根于他的时代情怀。金华经历过童年和少年的生活艰辛,改革开放后幸运地成为“天之骄子”,参与过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对祖国、对人民、对脚下的土地始终怀有深沉而缱绻的爱恋。他把这种爱倾诉在笔端、在诗歌里。在《拥抱深蓝》里,他歌颂中国航天事业,“这片深蓝,是一个天大的棋盘/田野的葱郁/工厂流水线的蓝领/大学城科学院的弧光/决策和设计者的蓝笔和蓝皮书/直至军营的墨绿/都揉进了这航天服的底色/绘就这万物逢春的时代长卷/于是,我深爱着这片航天蓝”。诗人巧妙地运用棋盘这一比喻,把田野、工厂、大学城、科学院、军营等等都熔铸在一起,铺就了航天蓝的底色,寄予了对祖国综合实力的赞美。在《来自南国的欢迎》一诗中,诗人另辟蹊径,为北京冬奥会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北京冬奥会/我们以中国南方的方式欢迎您/让南水北调送您一江碧水/让喜鹊衔枝送您一朵梅一个春天”,立意巧妙又自然贴切,一位南方诗人对北京冬奥会的欢迎之情跃然纸上。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金华在脱贫攻坚方面创作的诗歌数量占比大,比如组诗《朝花夕拾》《武陵山的梅子熟了》《续写山乡巨变新篇》《山区的花儿开了》等,每组诗都有独特的视角、精细的表达,汇聚在一起,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同时,在这场勠力同心的攻坚战中,诗人也展现了农民群众的自强不息精神。“好多词山里人似懂非懂/许多事让他们心烦/生锈的不止是砍柴刀/喊开会他们答要护林进山/填问卷调查的多项选择他们选择挑担//山里的空气/洗亮山里人的心和眼睛/他们分得清家猫和野猫/算得准时间和收入账/记得清每张蹲点干部的脸庞”(《金子村》),诗人在对扶贫工作热情赞颂的同时,也以山里人口吻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善意嘲讽,这反而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立体感。诗人的爱深深植根于他的故土情结。金华具有浓郁的故乡情结,这不仅是因为故乡的土地养育了他,还因为故乡承载着金华的诗人梦想、寄予着诗人的人生观念、传承着诗人的文化理想。三湘大地、洞庭四水,这里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脉底蕴、代代相传的伟人故事、至亲至爱的亲朋好友。在诗人笔下,千溪成河、万川归海,成就了既大气磅礴又温婉细腻的诗国海洋。在《涟河颂歌》《左公故里怀古》等组诗里,诗人追寻着英雄的足迹,抒发着时代的怀想。在《为父亲写墓志铭》《母亲印象》《散落天堂的爱》等诗中,诗人饱含泪水,为父母、为亲人画像,为生长于斯埋葬于斯的芸芸众生留下了诗的印记。这里,既有诗人撕心裂肺的追忆,又有沉潜发酵的反思。诗人是大孝子,对父母的孝敬恭从不时流露笔下。他在高铁上用手机改写父亲的墓志铭,“满载的车厢一下如无人的世界 / 整个身躯一如子弹头飞车 / 穿梭在时光隧道和父亲的心波 / 心汁压榨成二百碑文”(《为父亲写墓志铭》)。他向父亲承诺,“您去了,以往所有的好陡涨 / 涨成了记忆里的河 / 诗文里的泪 / 儿余生的一缕温暖 / 继续撑着敬母的源泉”(《思父》),年近花甲的诗人有着一颗讨娘欢心的赤子之心,枝枝叶叶中映射着大爱光芒。这部集子里,还有不少记游诗,也每每与故土相参照,在他乡之行中反刍故乡,别有一番滋味。我们还要注意到,诗人对故土的眷念中有时也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这不仅仅是岁月催人老的感叹,还有对耕读传家、孝老爱幼、感恩报德、勤劳坚韧等乡土文化式微的挽留。“我只想抱着这青石板路的腰痛哭一场 / 我的如青石般黛青的头发呢 / 我的如青石般黛青的记忆呢”(《青石板路》),“回不去了,时光 / 身上的汗水早已干涸 / 倒是笑容长留 / 在柴院主人的脸上”(《柴院》)。读这些句子,不禁叫人唏嘘。诗人尤其痛心疾首的是那些数典忘祖的人,“可从最熟悉的路上走出 /最容易忘了来时的模样 / 吃饱了便忘了饿忘了粮 / 穿暖了便忘了冻忘了布与衣 / 甚至从炊烟里走出要断炊烟”(《从炊烟里走出要断炊烟》)。诗人的呐喊犹如一记重锤,值得我们警醒。
诗人的爱深深植根于他的水利情感。金华长期从事水利工作,对水利怀有真挚的职业情感,治水管水兴水是他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所在,当然也融入了他的诗歌里,作为水利人,对此我感触尤为深刻。在组诗《在江汉大地》里,他站在丹江口水库大坝上,抒发着水利人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虔诚与自豪,“我是一个慕名而来的湘人 / 一个不拜武当要拜大坝的“香客”/ 观烟波浩渺的丹江湖 / 我愿是漫江碧透里的一尾丹江鱼”。在《烂泥湖的荣光》一诗中,他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拧紧裤腰带创造出了人间治水奇迹”的四十万治水“泥军”充满敬意,对今天“烂泥湖变成了国家湿地公园”的“新山乡巨变的风景画”给予深情歌颂。在《云端里的花海》里,诗人写道:“好花要有好水浇 / 高山流水涌进滴灌喷灌 / 一张节水网串起田野山岗”,倘若不是水利人,视野里很难出现这么一幅图画。水利并不是诗人自己的选择,而是祖国的需要、时代的召唤和人生的机缘,但诗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普通和平凡耗时正好一花甲 / 我们在《雷锋日记》里寻找勇气和诗意 / 把自己钉进了共和国大厦 / 永不生锈还待时间检验 / 时间也会检验出我们这代人生命的不悔”(《从螺丝帽到螺丝钉》),诗人的自况也是当代大禹的共同心声。
爱与情是水乳交融的,大爱就是至情。这本集子里,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写人记事,浓烈的情感抒发是其最显著的特色。诗人的爱是有根的,也是有形有状、有血有肉的;诗人的情是真挚、朴素、热烈、深沉的,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不凌空蹈虚。我想,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一是丰富的生活阅历。金华的生活经历十分丰富,又有一颗敏感诗心,有浩然之气。他的诗都取自日常生活,所到之处、所观之景、所思之人皆有诗意,因此,他的诗非常自然,随物赋形,率意而成,没有丝毫的拼凑堆砌,“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二是切口的精细入微。诗人的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不乏类似航天、冬奥会等宏大题材,但是诗人善于从细微处入手,运用细节来承载诗歌的旨归。特别是在《乡村工匠,远去的荣耀》这组诗里,对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外公一辈子酷爱石头 / 九十岁时还给自己凿了石墓”(《石匠》),仅此两句,就将一个老石匠的豁达胸怀刻画得入木三分。“远看背着一座山 / 近看背着一张琴 / 纺锤一响 / 棉花万两”(《弹匠》),熟悉早年弹匠生活的一代人,对“一座山”“一张琴”的细节比喻一定会拍案叫绝。三是语言的诗意营造。诗人钟情于实话实说、深入浅出。一首诗只有叫人懂了才能让人爱上,诗人深谙此道。但是,金华的诗歌也不是平淡无味的大白话,相反,正如他所说的,“努力写得有韵味和画面感”。通读诗集,我觉得他做到了。诗人选词造句很有讲究,语言注重及物性,许多词语具有浓郁的湖湘标识,既凸显了地域文化特色,也使得诗歌充满画面感;不少细节镶嵌在历史和时代中,彰显了逼真的现场感。诗人特别注重韵味的酿造,有些句子让人回味无穷,甚至忍俊不禁。比如“上坊村别联想上访 / 黄旗村可以联想黄金 / 胜溪村肯定今胜于昔 /有意思的是女村支书被叫成‘杨门女将’”(《粟裕故乡的油菜花》),通过谐音的联想和对比,活脱脱勾画出堡子镇的可喜变化。类似这样生活气息浓厚、诙谐幽默的语言在诗集里俯拾皆是。
在一篇小文里对金华的诗歌进行条分缕析是不可能的,但仅以我初步的阅读,就能感受到这是一部叫人击节称赞的好集子。这一切,都再次证明,诗歌要扎根时代、扎根生活、扎根群众。“我来自南方的乡野 / 一只吃惯了竹根竹笋的竹鼠 / 一尾习惯了水田旱田的泥鳅 / 一条闻惯了汗臭和香火味的家犬 / 我的灵魂属于我的那片土地 / 前世今生注定是一个乡巴佬”(《一个流浪在城里的乡下人》)。“乡巴佬”胡金华是一位有底气、有追求的诗人,我祝愿他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继续精耕细作,为诗坛带来更多的惊喜。
李训喜
2023 年 4 月 16 日于北京
李训喜,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兼水利作协主席。
后记
我的诗歌之路
我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文字的搬运工,可我始终怀揣着一个当诗人的梦想。
我一直认为:写诗和画画一样,是要有天赋的,既有智慧的,也有经济的。天赋乃天成,一个农民的儿子,居然爱上了缪斯,就像穷小子想娶天仙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几十年走过来,我就这么深爱着,自己都佩服自己。
大约是1978年冬天,在双峰一中的阅览室,偶然间翻到一本《中国近代史》,现在都记得那蓝白相间的封面,很干净很秀气。如获至宝的我一口气读完,读到愤慨时写了首长诗抒怀。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写诗。此事老师并不知晓,但不久就扯出了问题。起因是借读同学的《曾国藩家书》,一股脑钻进了曾国藩的世界,又写诗了,为他叫屈。这两首诗经同学一传播,被老师知道了。那个年代“曾剃头”是不能谈论的,结果挨了政治老师批评。班主任谢立凡老师和历史老师曾彩初校长都是我一生非常敬重的老师和长者,分别找我谈话,善意提醒:马上就要高考了,不要分心,莫要影响考试。可我天生犟驴,哪听得进?父亲得知,专门从乡下来学校训我。我竟想说服他:没有曾国藩,至少没有家乡的崛起。气得父亲对我连骂带踢。好在老天保佑,我在病中参加高考,虽然超了本科线好远,结果考了个大学专科,但是进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中文系。一个作家和诗人梦就这么悄然诞生了。
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崽女不要在外人面前说自己没有,再没有还有一双手,去外面闯荡时,要打落牙齿往肚里吞。那时,家里走亲戚,母亲总是大包小包,其实大多是带着一堆衣服。去的时候,找个弯或无人的地方,把补丁加补丁的外衣换成稍微好一点的,回来时又换回。每年春节,我总要在走马街大丰塅的田埂下换两次衣服,因为不远处就到了父亲的姑妈家。总感到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挨冻的印象十分深刻。小时候缺粮缺钱的感觉很不好,所以考大学填志愿时,有生活费和助学金的师范院校就是最好的选择。入校后,从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学费、路费,还要挤出买《人民文学》《诗刊》等的钱。那个年代,诗歌风靡,诗人时兴。我一头长发,故意蓄起嫩嫩的胡须,还总是抱着一叠书,头向着天,像个精神病患者。一有时间,我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后山的油茶树里,吟诗作文。偶尔,在油印的校刊上发首诗,也能激动几天,还经常偷偷地去传达室看有没有印着报刊函的回信。大学毕业不久,我就在湖南和云南等地刊物上发表散文、诗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的生存总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农家子弟,不仅自己要生存,同时还寄托着一大家子的生计与希望。1982年7月大学毕业,说是分配我回家乡县委机关工作。我就安心在老家一边插田扮禾搞“双抢”,一边等分配。一个多月后,我挑担箩筐到二十外的永丰街上卖东西,遇上一同学。他惊讶我还在挑担,而他早在地委机关工作,拿了头个月工资。他问我:“你那么幸运被省直机关看中了,怎么还没去上班?”我将信将疑马上跑邮局打电话跟学校核对,他们也惊讶,说确有其事,通知书早已寄出。于是立马到县邮局查,好半天才查到挂号存单,通知书已在很早前就投递给走马街区邮政所了。我忙借辆自行车,搭着箩筐,到二十里外的区邮政所。马路边的邮政所里空无一人,幸亏知道这个所长兼邮递员的名字,问了好几里地找到正在田里扮禾的他。等从铺满灰尘的邮件中找到通知书时,天已黑。我又骑车到几十里的双涟火车站,连夜赶往长沙,身上的泥巴还没洗净就睡了。第二天清早,赶到厅里人事处。他们认为我不来了,并说是拒绝分配。好说歹说,来往于学校与厅局之间交涉,才被分配到了一无所知的离家天远的溆浦县大江口,省里直辖的大型化纤化工企业——湖南省维尼纶厂。它是当时省里的重点亏损大户,也是厅里最差的单位。报到了才知道我是进了长沙市户口的,进厅机关的名额正好被有关系的原应回工厂的人顶上去了。就这样,我跟大湘西怀化结缘,一结就是四十多年。
溆浦是一个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的地方。屈原流放至此,写了大量的名篇。溆水在工厂门前汇入沅江,流动着满河的故事。刚进厂时,家族里唯一的读书人我的表叔湘潭大学中文系老师王建章给我写信,要我去县城找找县文化馆的朋友,好好请教,莫荒废了文学。我去了,就结识了热心的作家馆长唐德佩、舒新宇。后来,又通过他们参加笔会,认识了文学青年王跃文、王行水、向继东等一批后来的大作家与诗人,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鼓励。在生产车间苦闷的工作之余,继续写文作诗。同寝室的诗人向书毫帮忙抄稿投稿。两人发了豆腐块文章,拿到几块钱稿费,就买酒打牙祭。当年曾下放到维尼纶厂的《诗刊》编辑著名诗人王燕生还通信鼓励我们,信中就有一篇《长留群山的记忆》,我把它推荐到厂报发表。领导慧眼识珠,把我调入机关写公文。很快小有名气,口头命名为“工厂一支笔”。公文越写越多,头发和朋友越写越少。有时候该是其他部门和其他人完成的公文任务,也一定要交给我,以致别人对我的怨气越来越大,哪有时间和心境搞什么创作。1989年后当了个“小官”,后来又选调到地方,完全是行政事务。无论干什么都着迷的人,只能把文学梦怀在心中,四处奔波,为了工作,为了责任,当一个专业的职业人。但心底的文学梦从未泯灭,再忙也一直在偷偷地读诗,偶尔还偷偷地写诗,只是许多熟人都不知晓而已。2022年7月退居二线。组织谈话的当天,我关着门就开始写作。两天写完一篇散文,投出去居然发表了,并获得水利部的一个奖项。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写诗,先是上了“新湖南”,点击量颇多,后来居然上了《诗刊》等大刊。这样就有了这么一本诗集,算是了却人生一个愿望吧。
家乡名人璀璨,人才辈出,我深以为荣,自己无出息,只能沾光揩油。当年老校长曾彩初见我没考上理想的大学,特地来看我安慰我,夸我是“秀才”,我给改了个字——“锈才”。他哈哈大笑,说有诗意,可以当诗人。几十年过了,诗人没当成,还看不起有些诗风和有些所谓的大家,并不屑与他们为伍。去年有个刊物要求修改一首歌颂家乡河的诗。一开始,按捺不住名利心,按要求改了几次。后来要改中心思想时,我牛脾气上来,就一字不改了。读诗写诗我自定了三个原则:一是说人话。要让更多的人读得懂,要让读者知道你想说什么。现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恨不得一口气把所有路走完。一个字、一张图片在手机里,就想把要表达的全表达出来。其实在我们乡下,大人在你学说话时就会教育你:要是不让人听懂,你说话干什么?即使指桑骂槐,也还是要有人懂的。二是动真情。也许是真的老了,写作时我常常潸然泪下,有时难过极了,尤其是写家乡写亲人,写给远在天堂的亲人时。当然,表达感情的途径是多样的,探索方式永远在路上。我反感有些诗人的造作,更反感现实中“从炊烟里走出要断炊烟”的人。三是要有诗意。努力写得有韵味和画面感。我喜欢看画,看摄影。我的诗追求画面感,加上是一乡巴佬,普通话学不会,所以不一定好朗读。由于自己的学识和固执,诗很平凡又俗气,难登大雅之堂。但我本是一俗人,何苦要大鼻孔插根葱?何况现在还有点自知之明,还在不断努力,还在尽力而为去满足自定的三个基本原则。
能够重拾文学梦,非常感谢组织和一群朋友。特别要感谢工作最后的宿营地——水利系统,感谢水利部文协和作协,湖南省水利厅和水文化研究会。最想感谢因诗相识相知的《诗刊》主编大诗人李少君和水利文协副主席诗人凌先有、李训喜及部里老司局级领导陈梦晖等人的提携鼓励。能够出书,非常感谢深圳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还要感谢教育帮助过我的所有亲人与朋友,尤其是我妻子的默默付出。感谢长期帮忙整理文稿的助手肖勇、老乡记者赵志高等朋友。薄薄一本书,满满的都是情和爱。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这本书面世了,是我献给这个世界的一朵小花,希望读者多浇水,多批评指正,我都会一一铭记,在此鸣谢。我将努力吸收,争取以后写得好点,再有诗集出版。
胡金华
2023年4月8日于湖南怀化
责编:赵志高
一审:赵志高
二审:肖畅
三审:廖声田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