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28 14:4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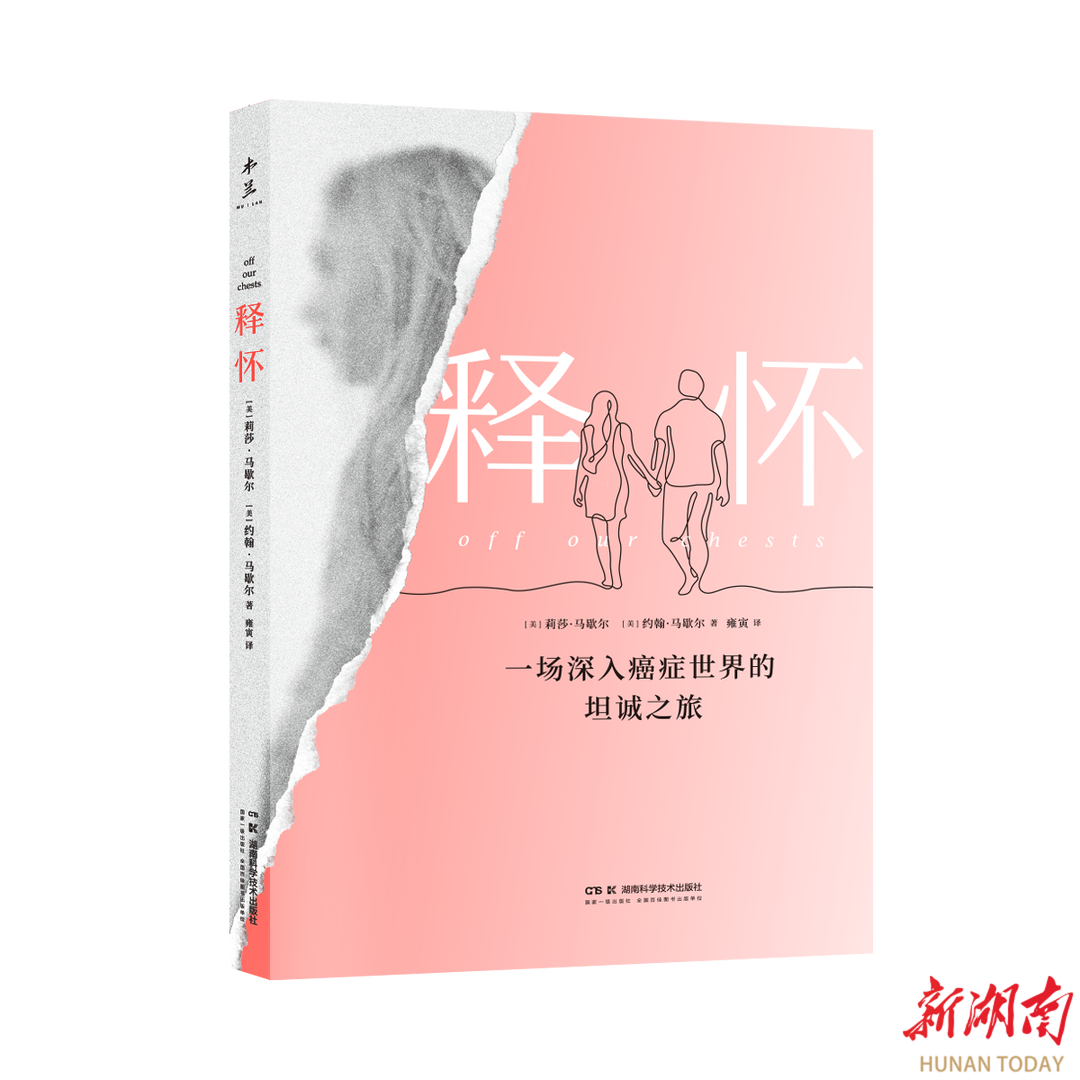
文|橙皮兔
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刻,是在手术室大厅外面的长椅上度过的。
头顶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焦急等待的间隙还要不时安慰四位面色苍白的父母——我的双亲与岳父母正像四片被霜打过的叶子般瑟缩着。
手术时间真的很长,三个小时过去了,医生打开门要我进去却只告诉我“肿瘤物已经切除,但活检才做完,并不能确定是恶性还是良性,请家属签字决定是否切除一侧卵巢?”
如果是恶性,需要马上切除,如果今天不切除,意味着马上面临二次手术;如果是良性,那切掉一侧卵巢将影响她的妇科功能。
签字笔悬在手术同意书上,墨迹在"恶性/良性"的选项间徘徊,而彼时我们尚未拥有自己的孩子。
那时我刚卸下教育媒体人的身份,猝不及防地成为癌症家属。
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当妻子健康良好的接送幼儿园的儿子回家,当新工作的电脑屏保换成全家福,翻开《释怀:肿瘤医生与乳腺癌妻子的癌症世界坦诚之旅》时,书页间流淌的勇气让那些消毒水味的记忆突然有了温度,也让我明白:癌症或许能撕碎生活,但永远撕不碎那些紧紧相扣的手。
在癌症面前,我们都是学生
《释怀》开篇就让我的眼眶泛起潮意——肿瘤科医生约翰在妻子确诊乳腺癌的深夜,颤抖的手写不出一份完整病历。
这多像2019年的我啊!
在妻子确诊卵巢癌的病房里,手机屏幕映着我不断搜索"五年生存率""复发风险"的侧脸,那些冰冷的专业术语化作千万根钢针,将我们精心构筑的未来扎得千疮百孔。
正如书中莉莎描述的:“确诊时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必须在一无所知中做出生死抉择。”这位43岁的律师妈妈,在书中坦诚记录了自己面对三阴性乳腺癌时的恐惧:要不要参加临床试验?是否接受双乳切除术?怎样告诉年幼的孩子“妈妈可能会离开”?这些揪心的自白,让每个癌症家庭都看到自己的影子。
而约翰医生的视角更让人震撼。当他从医生变成患者家属,才真正懂得“化疗方案里没有写明的代价”:妻子因脱发拒绝照镜子时,他偷偷买来十二顶不同颜色的假发;听到止吐药价格时,他第一次为医学的无力感落泪。
书中有段话直击人心:“作为医生,我治愈过无数人;作为丈夫,我却治不好爱人的失眠。”
我记得,妻子第一次化疗的那晚,我蹲在病房厕所里吐了。消毒水混着呕吐物的味道呛得人窒息,但我不敢出声——她正因药物反应蜷缩在床上发抖。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疾病击溃一个人时,连带着会把全家拖进战场。
就像《释怀》中的约翰,我自诩是个“文化人”,读过的书堆满三面墙,却在癌症面前像个文盲。我不知道化疗后该给她煮白粥还是南瓜汤;分不清血小板降低和白细胞减少哪个更危险;甚至会在她疼到咬破嘴唇时,慌得打翻水杯。
某天深夜,妻子攥住我的手:“老公,我觉得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我还没有为你生下一儿半女,老公,我觉得你是最懂我的,我从手术室出来,你知道我醒了,却不能动弹,在那一刻知道我听到外面嘈杂的声音特别难受,你要我妈和你妈赶紧别哭……”
她手腕上埋着PICC管,声音虚弱,眼睛却亮得惊人。
回忆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释怀》里的一句话:“癌症是一所最残酷的学校,但毕业时,你会带着爱的学位。”
治疗室里的史诗:那些狼狈却发光的日常
如果说抗癌是场战争,那么《释怀》记录的绝不是英雄凯歌,而是战壕里最真实的泥土与星光。
莉莎在书里写化疗后去超市,发现假发里藏着的输液管吓哭了小孩。她没有逃离,反而蹲下来对孩子说:“阿姨在玩宇航员游戏,这是连接太空舱的管子哦。”
这种带着泪的幽默,让我想起妻子第三次化疗时,顶着光头裹碎花头巾扮“包租婆”的模样。正如书中写的:“癌症家庭的浪漫,是消毒水味里开出的野蔷薇。”
书中无数细节让人破防:
约翰把苦药片磨成粉混进草莓奶昔,因为莉莎说过“苦得想吐”;夫妻俩缩在CT室外的长椅上,用耳机分听《You Raise Me Up》;女儿用蜡笔在镜子上画眉毛,歪歪扭扭写下“妈妈最好看”……
这些片段让我想起自己那些笨拙的温柔:学煮入口即化的南瓜粥,笑着说妻子麻药醒后的呕吐物的味道像极了她爱吃的螺蛳粉的气味,在呕吐盆边我写着古体诗,把孕检报告和化疗单钉在同一本文件夹里——原来爱在最狼狈时,反而会显露出最原始的坚韧。
在死神的凝视下,种出一个春天
《释怀》最动人的章节,是莉莎康复五年后的某个清晨。她煎着鸡蛋突然转身说:“我现在连消毒水味都觉得亲切——这是活着的味道。”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让我想起2021年儿子出生时的场景:产房飘着熟悉的酒精味,但混进了新生儿的奶香。同一家医院,同一个手术大厅,甚至连手术的专家医生都是同一拨人(妇科产科是一个大科),妻子用曾经植入管PICC管的手臂抱着娃哺乳,笑着说:“癌细胞想不到吧?这副身体还能创造生命。”
这种向死而生的力量,正是本书的灵魂。
约翰作为肿瘤专家,在书中穿插了大量乳腺癌科普:从化疗原理到临床试验伦理,从义乳选择到医患沟通技巧。
但他说:“最想告诉读者的不是医学知识,而是在绝境中保持希望的能力。”
书中有个震撼比喻:“抗癌就像在暴雨中护住火种,你可以被淋透,但绝不能松手。”
在医学与人性之间,找到抗癌的第三种答案
作为媒体人,我阅读过无数健康类书籍,但《释怀》是特殊的。它不像医学指南那样冰冷,也不像心灵鸡汤那样悬浮。
它还包括:多角度叙述的癌症诊断—治疗—康复故事:妻子的患病体验自述;丈夫的照护体验,作为肿瘤专家的公众演讲,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乳腺癌家庭患病、治疗、互相关心的图景;
多重身份的叙述者带来的丰富情感层次:肿瘤学家/患者家属的多重身份,在家属患癌过程中进行医疗选择以及职业思考的体验,为读者的医疗选择提供了现实的参考;
真实可感的疾病书写:患病到愈后的一段完整历程,包括止吐、假发等等非常影响患者生活的问题的处理,让已经或即将面对疾病的人群知道自己跟家人即将面对的处境,并提供积极的信息;
乳腺癌治疗相关的基础科普:除了最重要的癌症研究、治疗相关信息,也传授了许多帮助人们去看待疾病,与家人朋友沟通病情,处理工作事务等等的技巧。
更珍贵的是那些“无用之用”:莉莎列出的“化疗日快乐清单”(第3项是“允许自己哭15分钟”),约翰写给患者的30句“废话文学”(比如“今天太阳很好,说明光合作用打败了黑夜”)。这些恰恰是医学教材里找不到的生存智慧。
当故事变成星光:我们的伤疤,你的火把
后来的日子,妻子常抱着两三岁的儿子讲她抗癌的故事。他会说妈妈曾经是一位光头阿姨,妻子就在旁轻笑:“宝宝,你要和爸爸妈妈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读完《释怀》的那一刻,我合上书,眼泪止不住地流。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书中那些细碎却滚烫的瞬间——化疗室里丈夫紧握妻子的手,深夜病床边孩子画下的“妈妈加油”,餐桌上全家人强忍泪水却依然笑着分食的一碗粥……这些画面让我突然明白:癌症能摧毁身体,却永远无法打败一个被爱包裹的家。
莉莎在书里写过一段让我揪心的细节。化疗后她头发掉光了,连眉毛都稀疏得几乎看不见。她不敢照镜子,甚至拒绝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直到有一天,她的小女儿偷偷用蜡笔在镜子上画了一对弯弯的眉毛,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妈妈最好看!”莉莎说,那一刻她突然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原来爱可以这样具体,具体到一根蜡笔、一面镜子、一双孩子的手。
而约翰的故事更让人揪心又震撼。作为肿瘤科医生,他见过无数生死,但当妻子成为自己的病人时,他第一次在诊室里手抖到写不下病历。他说,最难的从来不是制定治疗方案,而是深夜听着妻子因疼痛蜷缩在床角的呻吟,自己却只能一遍遍揉着她的背说“我在”。可正是这样的时刻,让他更坚信:“医学能延长生命,但只有爱能让生命真正活着。”
爱是什么?
是约翰偷偷把妻子的化疗药换成草莓味冲剂,只因为她曾说“苦得想吐”;是莉莎忍着剧痛录下几百条语音,留给两个孩子“将来妈妈不在时,你们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是全家人在医院走廊里抱成一团,哭着说“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这些细碎的甚至狼狈的瞬间,拼成了癌症家庭最真实的模样。没有英雄式的壮举,只有普通人的咬牙坚持;没有奇迹般的转折,只有日复一日地“再试一次”。但正是这样的平凡,才让希望变得触手可及——希望不是等来的奇迹,而是每个清晨睁开眼睛时,依然选择相信“今天会好一点”的勇气。
如今儿子总喜欢摸着妻子腹部的疤痕问:"这是妈妈打怪兽的勋章吗?"
我和妻子会笑着回答他,告诉他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两场战争,一次叫“死”,一次叫“生”,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
真正的释怀,不是忘记痛苦,而是学会在伤疤上种出花来。
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至暗时刻,我想对你说:
看看窗台上那盆蔫了又开的花吧——它和你一样,曾被风雨打折过腰,但根还扎在土里;摸摸口袋里家人塞的暖宝宝吧——再冷的天,总有人想捂热你的手;听听夜里病房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吧——那些和你一样在与命运拔河的人,都在陪着你。
《释怀》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它告诉我们癌症有多可怕,而是它让我们看见:当死神站在门外时,人类能用爱在门内种出一片春天。
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攥着报告单在百度里越搜越慌;在化疗室和幼儿园家长会间疲于奔命;深夜听着监护仪声响不敢入睡……
请打开这本书。
你会看见:“止吐食物地图”“疼痛分级自测表”,你也会看见:爱、希望与力量!
请记住:“当你说不可能时,请看看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其实是若干个抗癌家庭共同写下。
《释怀》现已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不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而是无数双手从深渊递出的绳梯,当我们无法给你一个拥抱时,愿这些文字能捂住你冰凉的指尖。
(本文作者为《释怀:肿瘤医生与乳腺癌妻子的癌症世界坦诚之旅》读者,2019年,其爱人查出卵巢癌并进行了切除手术,而后进行了四次化疗,2021年正常怀孕生下小孩)
责编:黄煌
一审:黄煌
二审:易禹琳
三审:杨又华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