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琴键 谭宇森 2025-03-21 16:2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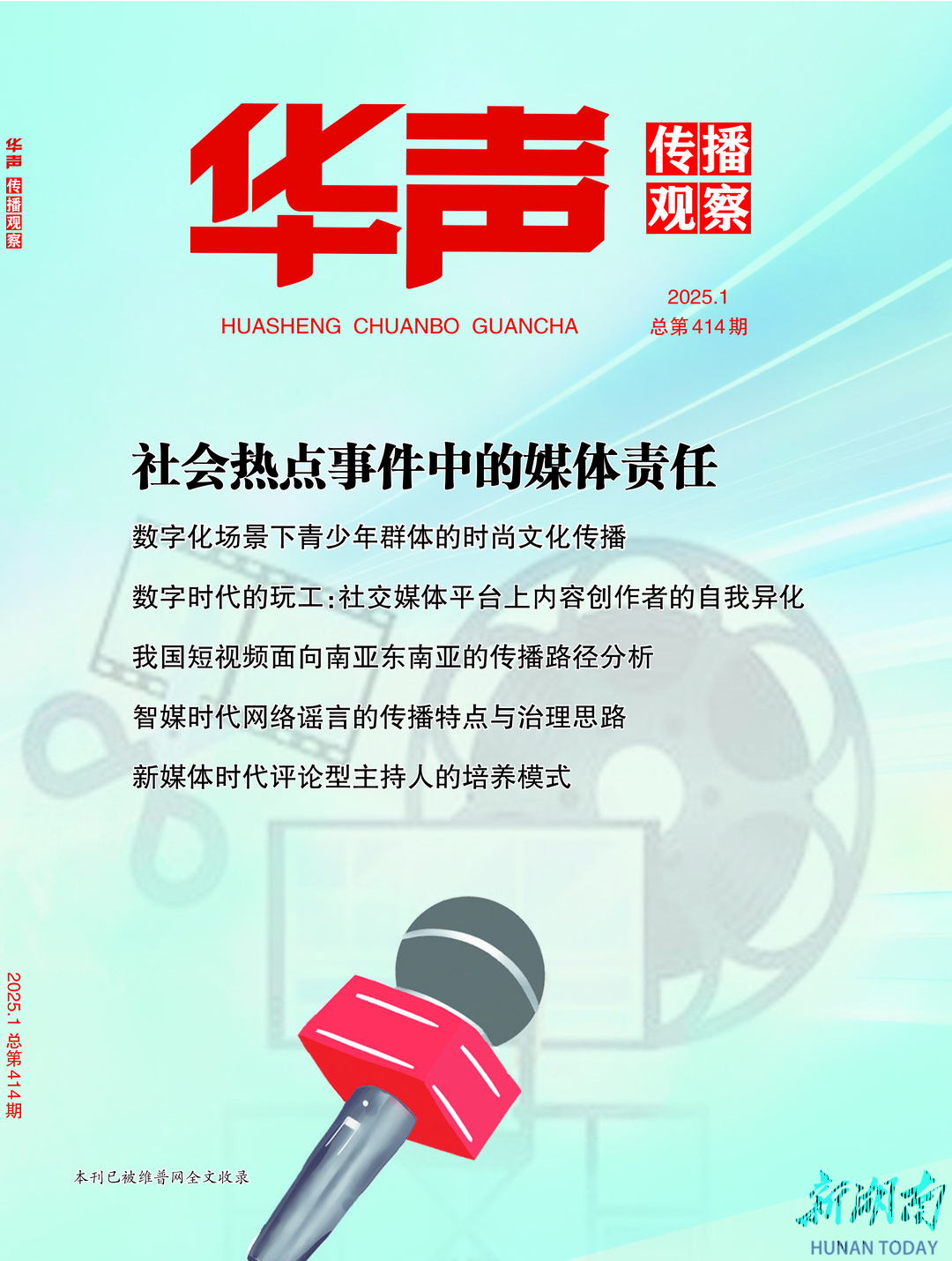
文/文琴键 谭宇森
数字化时代,微博、抖音、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与娱乐模式,也重新定义了内容创作与劳动的关系。在一些休闲的创作活动中暗含了服务平台、进行自我营销的劳动过程,产生大量的“玩工”(Playbour)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异化理论,尤其是自我异化的视角,为理解创作者在算法压力、市场需求与观众期待交织下所面临的身份疏离提供了批判性框架。然而,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经济收益或技术性约束,尚不足以解释创作者如何体验并理解这种新型劳动,以及在追求个人表达与社会认可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自我身份冲突。
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内容创作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历自我异化的具体表现与成因,并聚焦其对创作动机和身份感知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玩工的源起与研究回顾
玩工这一概念最早由爱尔兰学者库克里奇提出,他将这个词定义为通过游戏无意识地为游戏厂商劳动的玩家[1]。研究发现,玩工这一现象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体现了游戏玩家在不自觉中成为游戏开发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的现实[2]。“玩工”指向数字平台上劳动与娱乐日渐模糊的现象,尤见于社交媒体内容创作:创作者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也在进行具有经济或商业价值的劳动[3]。
国内学界对于玩工的研究,主要有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思考。学者邱林川首次将玩工概念引入国内,他认为“在内容生产的宏观结构上,网民们无力真正参与互联网服务商和内容商的决策过程”[4]。另有学者分析了游戏、社交、网购平台的相互促进与叠加,认为平台企业不仅从玩家获取有价值的私人信息,也利用玩家作为“你媒体”参与推广营销,从而节省大量运营成本[5][6]。三位学者探讨了游戏平台方(代表资本)与玩家(代表劳动力)之间关系的演变。
(二)劳动异化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异化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强调了劳动异化的观点,认为人类创造的世界与其创造者形成了敌对和对立的关系,从而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存在。
自我异化源于劳动异化理论,强调个体在劳动过程中与其活动、成果乃至自我身份的疏离。当创作者为迎合平台算法或观众需求而背离个人兴趣与创造力时,便易陷入强烈的自我异化感。数字时代,劳动异化包括了多重维度,主要分为劳动主体、劳动产品、劳动行为以及劳动关系的异化现象。汪金刚指出,资本逐利、信息技术扩张、个人时空被数字裹挟以及监管滞后共同导致了数字劳动异化[7]。随着网络平台和内容创作模式兴起,刘海霞认为创作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疏离未得到根本缓解,甚至因平台算法与市场逻辑的干预而进一步加剧[8]。与此同时,徐婷婷认为平台策略与劳动者主体性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数字劳动中的异化程度,提示我们应更关注创作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9]。
尽管玩工与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劳动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现有文献对社交媒体内容创作领域的关注仍有限。如何将玩工现象引入内容创作背景,探究创作者在何种程度上陷入劳动异化及其背后成因,尚待进一步研究。多数研究聚焦于平台经济与技术约束,却忽视了创作者如何具体体验和理解自我异化,以及这一过程对创作动机和社会互动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异化理论视角出发,审视社交媒体作为特殊“工作场所”如何塑造创作者的实践与身份,分析数字劳工的特殊形式——玩工在哪些方面体验到自我异化?这种异化是如何发生并深化的?又怎样形塑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创作行为?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本文希望拓展劳动异化理论在玩工现象的应用范围,也期望为平台生态的优化提供学理支撑,并为内容创作者、平台运营者更好地应对自我异化现象提出可行的策略参考。
二、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玩工”与自我异化
在数字经济与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内容创作者将兴趣与工作相结合的现象日益凸显,学界将其称作“玩工”或“娱乐化劳动”。创作者在“玩”与“工”交织中既享受兴趣驱动,又承担平台和市场所带来的商业化压力。表面看来,创作者似乎能灵活结合兴趣与谋生手段;但当个人表达被平台算法、观众期待及市场需求裹挟时,“玩”常退化为高度受控的“工”,潜藏自我异化的风险。
(一)内容创作的劳动性质
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短视频平台等)为个人提供了展示创意和分享内容的空间,也为“玩工”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场域。创作者在“玩”中投入热情与创造力,又在“工”中承受经济与社会压力,这种活动形式逐渐成为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
1.劳动与价值创造
在传统劳动理论中,劳动者通过活动向产品或服务转化价值;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创作者的产出(如视频、图文)以吸引互动并带来经济收益。“玩工”由此将原本的兴趣娱乐纳入平台资本积累的进程,使创作者更易感到外部力量的牵引。
2.劳动的双重性质
内容创作兼具创意表达与经济活动的双重属性[10],既能带来“边玩边赚”的满足,又因外部力量介入而引发自我异化。观众偏好、平台算法与市场逻辑不断重塑创作路径,使得纯粹兴趣表达和商业收益之间往往产生张力。
3.自我表达与市场要求的冲突
当创作者为迎合平台算法及观众喜好而改变选题或风格,“玩”的自发性被“工”的被动性取代。这不仅损害创作者的原生创意,也加重对自我表达自由的损耗。当“玩”被资本与算法蚕食时,创作者难免感到初心渐行渐远。
4.劳动的不可预见性与不稳定性
市场趋势与平台算法的更新令内容创作充满变数,收益波动与不稳定性易给创作者带来心理和经济压力。其在“玩工”模式下虽收到兴趣驱动,却常被迫随风向转变而背离初衷,加剧自我异化。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现代劳动活动的复杂性,其中创意的自我表达与经济价值创造之间的张力,以及劳动的不稳定性,都让“玩工”模式成为自我异化的温床。
(二)自我异化因素分析
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异化往往由技术、经济、社会及心理多重因素交织而成。原本赋予创作者更多灵活度的“玩工”模式,反而在以下层面令他们面临被动和规训。
1.平台逻辑与算法控制
算法决定内容可见度与推荐路径,迫使创作者不断适应其偏好。一旦背离算法,流量与收入即受影响[11],进而动摇创作者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知。算法不透明亦带来不信任与身份消解。
2.市场化压力
对观看量、点赞与订阅数的追逐易使“玩”转变为高度工业化的“工”[12]。若坚持自我兴趣或失去市场认可,若迎合市场又背离初心,典型地呈现自我异化。此内在张力亦将创作从单纯“兴趣表达”推向“商业敷衍”。
3.观众期待与反馈
正面反馈能增强动力,但过度依赖观众评价、甚至遭遇网络霸凌时,创作者会陷入对自我劳动与身份的怀疑。乐趣被无限迎合替代,令“玩”沦为迎合他人意志的容器,进一步加深对自我价值的质疑。
4.创作自主性的缺失
商业模式、算法优先级与用户需求的叠加使创作者丧失对作品的独立把控,陷入心理与身份的双重危机[13]。个人意志易被流量逻辑所取代,令原本富含自我实现意义的劳动逐步异化为被动生产。
上文提及的四种因素共同构成了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自我异化的复杂图景。将“玩工”视角融入其中,更能凸显创作者在工作与娱乐高度交融的境遇中,如何在外部规则与内在冲突间逐渐失去对自我的掌控,从而深化对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认识。
三、社交媒体平台上内容创作者自我异化的表现与影响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内容创作者的自我异化呈现多维度特征,涵盖个人心理、社会关系与经济因素。许多创作者最初怀着兴趣或娱乐动机加入平台,希冀将“玩”与“工”相结合,然而在实践中却面临多重压力。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中,自我异化不仅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疏离,也涉及劳动过程、人类本质及与社会他人的脱节。
(一)劳动者与成果的疏离
为迎合平台算法与外部指标(如点击率、观看时长等),原本具备个人风格与创意的作品逐渐被数据化与商业化。即使创作者收获大量互动反馈,仍可能感到作品被平台主导,而自身对劳动成果的掌控与归属感不断流失。
(二)劳动过程的外部控制
平台政策、算法逻辑与市场需求共同构成外部干预体系,使“玩”在“工”的绩效评估下日趋程式化。创作者为优化内容而频繁调整选题与风格,原本的自由创作心态因外部评判指标被严重挤压,进而对自身劳动过程和身份定位产生怀疑。
(三)与人类本质的脱节
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人与自我价值、潜能表达相联结的核心活动[14]。然而,社交媒体的商业化与流量导向往往迫使创作者背离真实兴趣与价值观,个人才能被牺牲,劳动意义与动机认同感逐渐式微,甚至出现创造力下降与自我怀疑。
(四)与社会他人的脱节
虽然平台可触及广泛受众,但互动多停留在浅层消费与评价。匿名性与负面信息的即时性加剧创作者的孤立感与被动性,同时激烈的商业化竞争侵蚀“玩工”合作潜力,使创作者在与观众、同行的关系中愈发疏离,影响其社会角色认同与自我价值感。
“玩工”模式下的创作者往往经历自我异化的多重维度,从劳动成果到劳动过程、从人类本质到社会关系均受到冲击。此过程不仅影响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满足感与职业发展,也折射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
四、减少社交媒体平台上自我异化现象的策略
自我异化在社交媒体创作环境中日益凸显,反映了内容创作者在“玩工”与平台规训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平台运营者在治理与激励机制上的挑战。要减缓这一现象,需要创作者与平台运营者共同努力:前者需强化自我认知与社群支持,后者则需在制度与技术层面确保公平与透明。
(一)内容创作者的策略
1.提升自我意识
创作者应理性审视自身创作动机及社交媒体使用方式,识别可能导致异化的行为模式,如过度迎合平台算法或追求用户参与度而偏离真实兴趣[15]。定期反思与自我评估可帮助保持对工作和自我满足感的掌控。同时,通过记录创作历程和情感体验,创作者能更好地识别内外需求的落差并加以校正,有效减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2.发展多元身份
鉴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单一身份可能导致创作者在面对挑战和失败时感到更加脆弱,建议创作者在多个平台和现实生活中寻找或发展多元化的兴趣和身份。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对任何单一平台成功的依赖,还能提供更广泛的自我表达和实现机会,从而减轻自我异化感。
3.社群支持与合作
构建或参与支持性的创作者社群对于减轻自我异化现象至关重要。通过分享经验、资源和策略,创作者可以感受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孤立感。合作项目不仅能够提高创作的多样性和质量,还能够增强创作者对自己工作的控制感和价值感。
(二)平台运营者的策略
1.透明的算法和政策
提高推荐机制与收益分配的透明度,让创作者明白影响内容可见度的核心因素,以免盲目迎合不透明的算法逻辑。清晰的政策沟通也有助于增进信任。
2.公平的激励机制
通过公开、合理的收益分享和多维度激励体系,平衡平台商业利益与创作者劳动价值。对优质内容的客观认可与奖励可减少因付出与回报不对称产生的异化感[10]。
3.创作者发展支持
提供培训、市场洞察及福利等资源,帮助创作者提升专业能力与自我效能感。平台若关注创作者心理健康与福利保障,也能有效降低他们在“玩工”环境下的焦虑与不安。
创作者需借助自我认知、多元身份及社群合作防止在算法与市场压力中迷失,而平台若能通过更多元化与人性化的机制推动公平与透明,则能在商业收益与创作者权益间取得平衡。唯有创作者与平台共同努力,社交媒体创作生态才会逐步迈向“双赢”,同时兼顾个体创造力、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福祉。
五、结语
尽管社交媒体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和商业机遇,平台规则、用户偏好与商业逻辑的多重挤压往往令创作者在劳动成果与价值追求之间产生冲突。通过分析与探讨,本文揭示了当“玩”与“工”高度融合时,创作者不仅在创作成果和过程上感到疏离,也在个人身份与社会关系层面经受压力。
为减缓这一异化现象,本文提出从内容创作者与平台运营者两方面着手,以在商业收益与创作者权益间寻求更好的平衡。数字经济和新兴技术将继续塑造内容生产模式与劳动关系,也愈发凸显对玩工与自我异化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的重要性。通过进一步的学术探讨和多方合作,数字创作生态有望朝着更健康、公平和富有创造力的方向发展。
(作者文琴键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资深记者;谭宇森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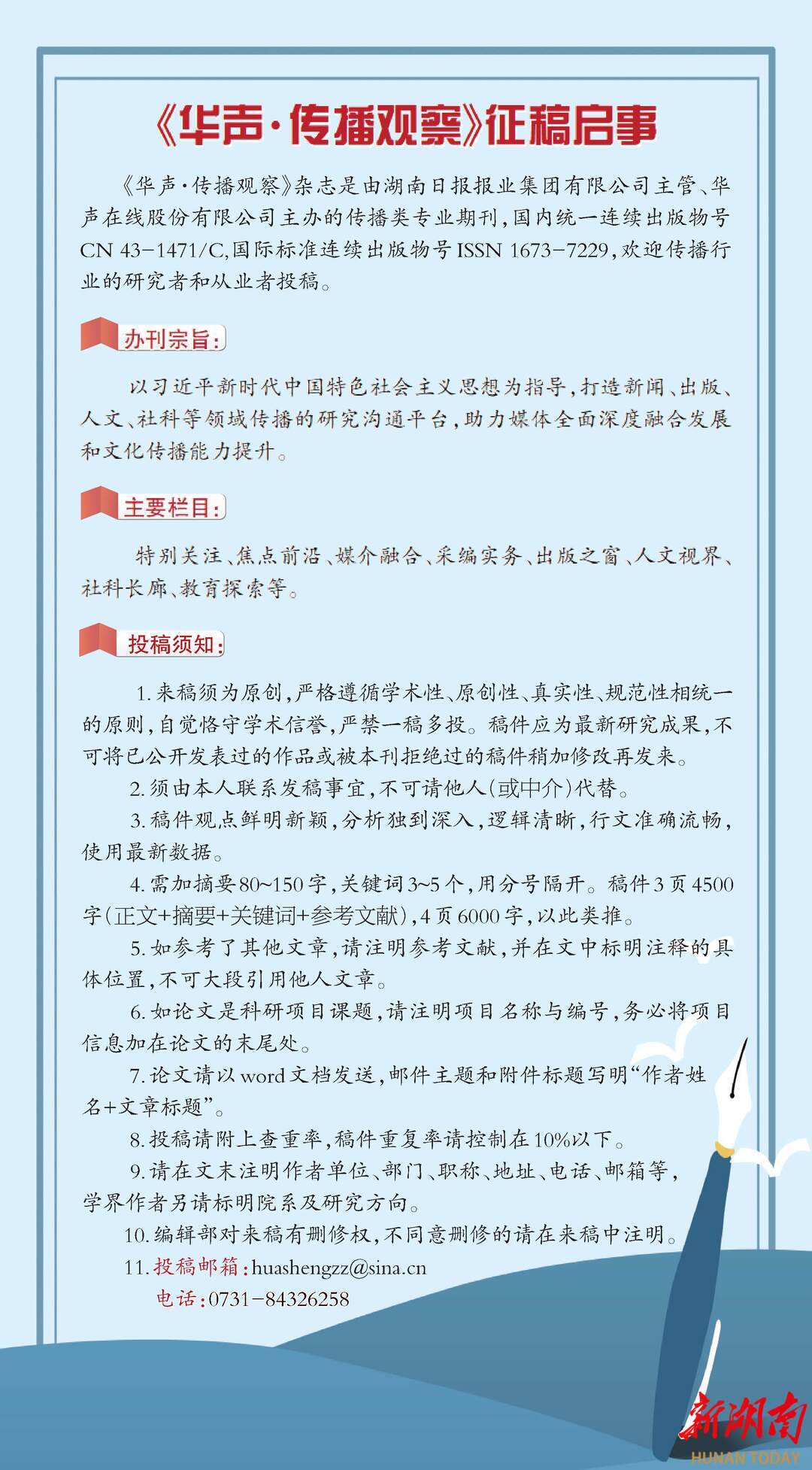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