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娥 2025-03-31 15:5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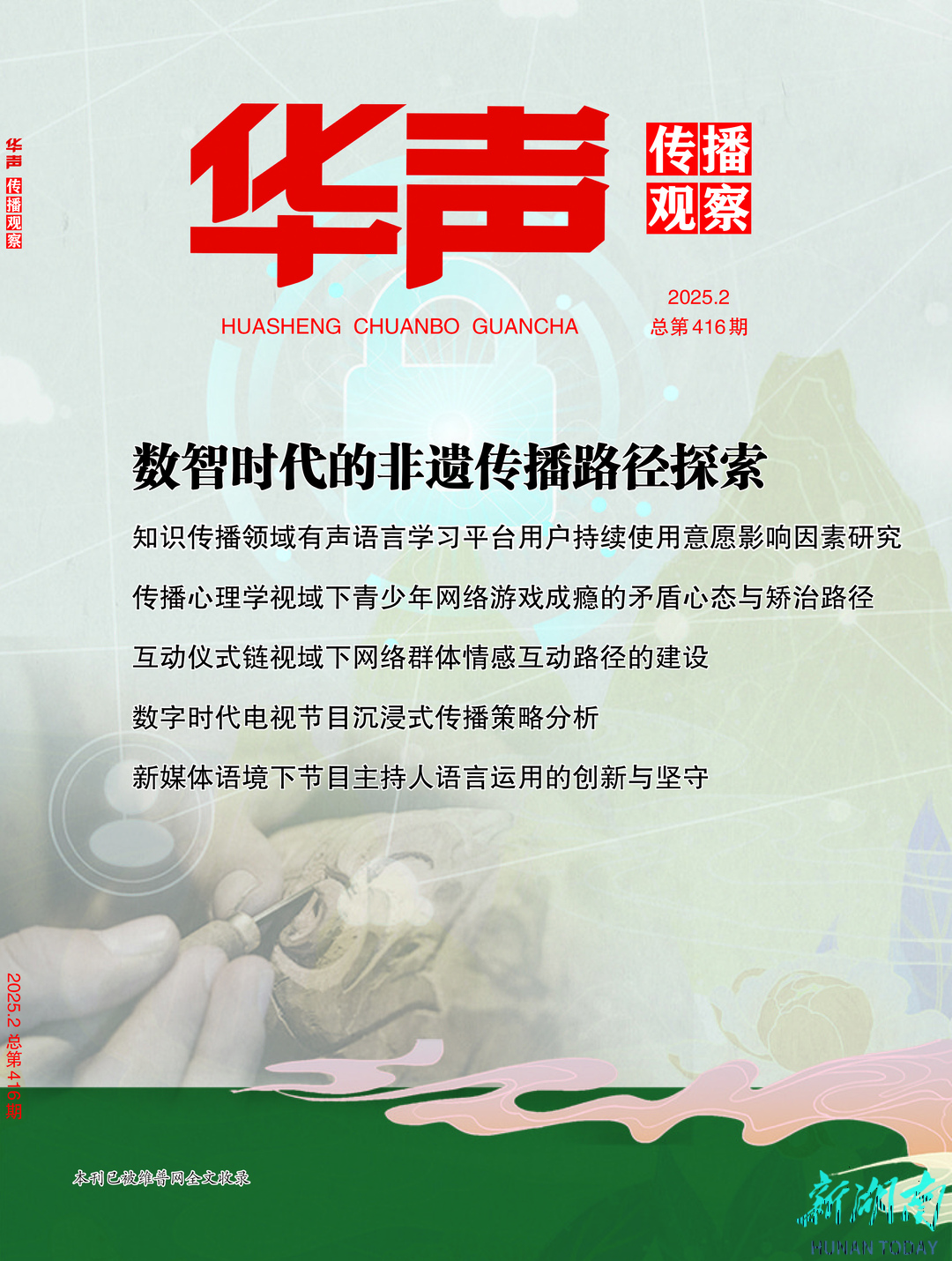
文/郑明娥
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人在对象性活动(如认识和实践)中,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以及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通过对人物、故事情节的描述表达传递自己。刘再复指出,“文艺创作要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的主体性,这就是要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作家通过对“实践中的人”的书写,对现实进行形象表达,也对人类精神进行终极追问,因此,充分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意识。
所谓历史题材,是指以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而创作的一类小说。邓宏顺的新作《九考魏源》就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既包括创作时对历史素材的拣汰组合,对“虚”和“实”的处理,也包括作家所持的文艺观、审美观、政治观、历史观,还包括作家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阐释与弘扬,对当代社会思潮和受众心理的把握和导引等多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历史小说《九考魏源》的创作,叙写了魏源从拜师求学、参加科考、做幕僚,到为官,到著述《海国图志》、最后离世的整个人生,展现了他历经挫折考功名、全力以赴做幕僚、费尽心思殚精竭虑办实事的奋斗历程,反映了他从昂扬奋发到压抑苦闷的精神状态。主要从以下方面体现了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相结合
小说《九考魏源》选自历史题材,作家创作时严格尊重史料,讲究历史真实,但同时小说的体裁属性要求文学真实,这样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相结合,体现出作家的自主意识。
(一)历史真实的表达
这里的历史真实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和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自我们承认的历史,历史本质的真实“是指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将历史人物、事件放在其所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表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文本中,我们读到作家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严谨态度。为了准确再现晚清的社会时代和魏源的人生命运,作家须拥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储备。作者在“邓宏顺长篇小说《九考魏源》新书发布暨分享会”上介绍了自己创作的缘起、过程和体会:为了创作小说,作者多次参观魏源故居,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历史文献等资料。在掌握扎实史料的基础上,魏源生活的时代和人物形象不断鲜活起来。作者反映了晚清社会现状:政治腐败,体制陈旧,思想落后,社会阶级矛盾此起彼伏,民族矛盾激烈。晚清漕粮河运、水利、纲盐等改革,太平天国起义,夷敌入侵迫使清朝谈判,割地赔款,而魏源就生活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时代,从小好学、入私塾、拜师求学、参加科举考试、到开启幕僚人生,后考取进士,任东台、兴化县令、高邮知州、著述《海国图志》等,大的社会时代、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和小的家风家训、人生轨迹都严格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进行创作。
以邓显鹤带魏源去京都求学的内容为例,沿途所经过的地方资江、岳阳楼、武汉、黄鹤楼、京都,清廷镇压多地叛乱,这里的时间、人物事件、途经之地,都与史料记载相符,作者遵循“大事不虚”的原则,尊重历史,反映出历史真实。作者将历史人物、去京都求学、所到之处、沿途所见放在清廷重兵清剿天理教起义这种历史背景中进行书写,符合历史发展逻辑,更能体现宏大的历史背景。因为清廷镇压多地起事者,加之黄河泛滥导致多地灾情严重,所以遍地凄凉、民不聊生,官民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这种敬畏历史、坚持历史真实的背后,体现出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体现出作家对历史真实的自觉追求。
(二)文学真实的书写
所谓文学真实,则意味着作家要有极其敏锐的眼光,在坚守历史真实前提下,进行合理想象,大胆虚构,深入历史人物内心,捕捉心灵深处的细微颤动,赋予历史人物故事以现代意义,这就离不开主体意识。对历史小说进行文学想象和艺术虚构的前提是“合理合情”。“所谓‘合理’,就是写作者一定要摸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这种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运动规律;所谓‘合情’,就是写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这种运动轨迹,只能遵从,而不能随意违背。”以“北上京都”为例,如果局限在时间、人物、事件、地方的真实性,就违背小说创作要求,这就要作家进行文学想象与虚构,于是作者虚构了一个情节:一个絮花披身的老妪拖着一个裸着下身的小儿前来乞讨,魏源给了他们一些碎银。这个情节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讨吃或活活饿死的现象时有发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生现状。此外,在小说中,为了突出魏源这个人物的典型形象,作家运用了逼真传神的行为描写、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独到精辟的议论,填充了很多细节,如虚构李详这个人物从带头闹事,到感谢魏源,反映了魏源深得民心、深受群众爱戴,这都“合理”“合情”。也有学者认为:人物言谈、空间描写、容貌服饰描写,是历史小说家营造历史氛围的三要素。这一点也是小说成功所在。作者突出了魏源作为儿子、朋友、官员等多重角色的对话语言;也细致地描写了别具江南水乡风格的宅院“小卷阿”“絜园”的地理位置、整体结构布局、取名等;也刻画了魏源的外貌。这些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感,让读者对文本中的“时代”和“人物”产生沉浸感和体验感。作家综合运用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法,给读者很强的代入感,让魏源这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些虚构的人物、情节、细节,是在历史合理性前提下的发挥和创造,具有文学真实性。
二、对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心理。创作主体的文化自觉,反映了作家内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担当精神。毋庸置疑,作家的创作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进而体现在作品人物对传统文化的践行和弘扬上。
(一)创作主体的文化担当
在创作理念上,作者从乡村题材小说向历史题材小说靠拢,创作主体身份上的认同,就是对传统文化身份的认同,作家以当代知识分子身份书写魏源这样的“湖湘士子”,形成传统文化身份的镜像认同。在题材上,作家选择历史人物魏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对魏源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发挥重大影响的认同。作家将其置于动荡不安的乱世中,表现历史变革潮流中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魏源从小就立下志向:立德、立功、立言。当科举一再受挫时,他开启了幕僚生涯,协助贺长龄、陶澍,编著《皇朝经世文选》,接着实地调查海运、水利、盐商;当鸦片战争发生时,眼见清朝政府不断妥协,他清醒地认识到改变国人思想的紧迫性,于是发愤著述《海国图志》;当他为官一任时,选择为老百姓谋福利。当然,作品也流露出对科举文化、官场生态的反思,魏源多次落榜,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人民。作家在此寄寓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要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从而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
(二)小说人物的文化人格
作者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以“同情之理解”,进行立体、全面的呈现,挖掘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精髓,将真善美呈现在读者眼前。魏源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自小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他传承了乐善好施的优良家风:出任县令时,以自己的俸银代缴历史遗留的债务;为官期间,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秉持“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尽显“民本”情怀,每到一处,了解民情,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兴化保稻”,就是描写他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保住下河七州稻谷的故事。魏源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国计民生大事,总体现出一种超前性和预见性,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认识到改变国人思想属第一要务,于是通宵达旦著书;魏源始终重视修身,追求治国安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他始终把修身著述和治国安民紧密结合。可以说,魏源是儒家文化人格的践行者,是仁义、礼仪、忠孝、至善、诚信的化身,是儒家文化的“精魂”。
作者将还魏源置于家庭、社会、科场、官场等很多场域中,反映了他的立体形象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如展现了他坦诚相待的友人形象;孜孜不倦的学子形象;刚正不阿的士子形象;勤政为民的官员形象;先知先觉的智者形象。魏源“求真”,对学问一丝不苟,能提出独到见解;对国家、人民一片真心,处处为国家和人民着想;对朋友一片真情,推心置腹;家庭夫妻和睦,孝顺父母,教育子女。魏源求“善”,这种善良就是仁义,“仁者爱人”。魏源求“美”,这是一种心灵、精神、道德境界的美。他乐善好施、著书立说、勤政爱民,无一不体现出他身上的德行之美。
三、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对话精神
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性,还表现在作家与历史人物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和交流,体现出一种对话性。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即人学,文学创作应该将“人”作为中心。历史小说创作应该实现写“历史的人”到写“人的历史”的转向,由叙述历史人物事迹,到书写历史人物的人格、人品、人情、人性,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探究。作家邓宏顺将笔触渗透到“历史的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书写“人的历史”及其生命意识,探索其生存价值、灵魂痛苦。作者在文本中体现了敬畏心灵的多层次对话意识。所谓“对话”,是一种双向的沟通交流,它的前提是理解。“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理解总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传递着在其中发生的语言事件。”[6]这种对话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历史的人”和“人的历史”的双重关注。由此出发,邓宏顺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对话意识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平视视角
作家善于以平等姿态对待笔下人物,就需写出有独立意识和个体价值追求的“人”。而文学与“人”的生命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文学与作家、作家所塑造的文学人物与写作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体现在文本中,作家聚焦于晚清魏源的一生,从“人”的自身发展角度,勾勒出一条近代化背景下传统士人艰难曲折、悲壮苍凉的人生轨迹,充分体现了人物的独立性、思想性和悲剧性。不同于仰视、俯视历史人物的小说叙事,作家以平视的对话姿态对待历史人物,以平视视角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展现人物的生存姿态、精神世界。作家全身心投入创作中,让历史生动起来,让历史人物活起来。这尤其体现在“兴化保稻”情节中,魏源为民请命,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与执意“开坝放水”的杨河督较量,与不断上涨的洪水较量,向陆总督求助,督促民众夜以继日地筑堤坝,魏源心系百姓的形象立即鲜活起来。作者还将魏源置于家庭、师友、朝廷、百姓、官员、科考等诸多场景中,以平等对话的沟通理念,塑造了一个为父慈爱、为友亲切、为官清廉、为子孝顺、为夫尽责的人物形象。
这种平等视角还体现出作家丰富的生命意识和人生感悟。围绕生命意义和价值追求展开人生轨迹,通过跨时空的生命对话,作家通过心灵领悟把握生命形式、生命价值,也依赖逻辑思辨和理性思维认识历史人物的生命世界。作家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真挚的感情引起读者的共鸣,又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发人深思,从而赋予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超越时代的文化哲理意义。在文本结尾处,魏源“死不瞑目”的细节刻画,让读者悲从中来,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把握。
(二)本真的生存状态
作家还表现了历史人物本真的生存状态。站在认同历史人物的立场,作家发挥生命体验的优势,深入解读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对笔下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展开叙述,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有时运用如椽大笔,将历史时代的风起云涌呈现眼前,让读者感悟历史人物背后厚重的历史和文化,读到“宏大历史”;有时运笔又精细入微,处处融入生命关怀,对历史人物的率真个性和命运遭际进行精准描画,让我们感受到社会时代给历史人物带来的精神与心灵的印痕,就是“小历史”。作者既将魏源置于漕粮海运、水利、盐政改革等历史大事件中,又将魏源拒绝见穆彰阿、到治水工地参与劳动时脚被冻土划破鲜血直流等画面展现得精细入微。这种通过“小历史”映射“大历史”的手法,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人物真实的生存状态。作者还将笔下人物置于生存困境、科考困境、治世困境中,力图写出人物负重前行的生命状态。在作品中,家庭的重担一次次压到魏源的肩上,从住所的租赁、购买、搬迁,到家人的生活开支,这就迫使魏源不得不授徒讲学、为人著述以维持生计。同时,充满艰辛的科考之路让魏源心力交瘁;任职裕谦幕府,治世良策不被采纳,让魏源深感壮志难酬;朝廷战败后,万般无奈,他一腔热血写《海国图志》,倾家荡产出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的结局。作家还原了他本真的生存状态:烦恼、忧虑、痛苦、焦灼、压抑、无奈、悲愤,深深震撼读者心灵。
(三)复杂的精神世界
作品还原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灵魂痛苦。历史小说既应“入乎其内”,深入历史,贴近历史人物,让人物扮演多重角色,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又要“出乎其外”,跳出历史,保持客观审视态度,不被历史人物带着走。这样才能写出历史人物内心动机的根源和外部环境加在人物身上的种种反应。在文本中,作家把叙述力量集中于历史人物的精神困境,写出了鲜活历史人物的生命律动和细腻真挚的情感。作品中,作家以魏源谋生、科考、为官、传播《海国图志》的艰难展示其内心价值追求、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精神痛苦。
卡西尔认为,只有超越了单一表现维度的情感特征,才能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多样化的运动……这样的艺术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那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摇摆的过程。”深入文本,我们既读到了魏源才学被认可时的喜悦,也读到了科考落榜时的难过;既读到了幕府人生中,编著书籍反响很大时的欢乐,也读到了良策不被采纳时的悲伤;既读到了他为官一任深得百姓爱戴时的心安,也读到了他看到《海国图志》出版传播反响寥寥时的心焦。人物情感的复杂性反映出精神世界的苦闷。可以说,人物塑造达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总之,作家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既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也体现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更以对话精神流露了对魏源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这都充分体现了《九考魏源》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
【基金项目:湖南省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怀化文学研究”(编号:HSP 2022YB93)研究成果】
(作者系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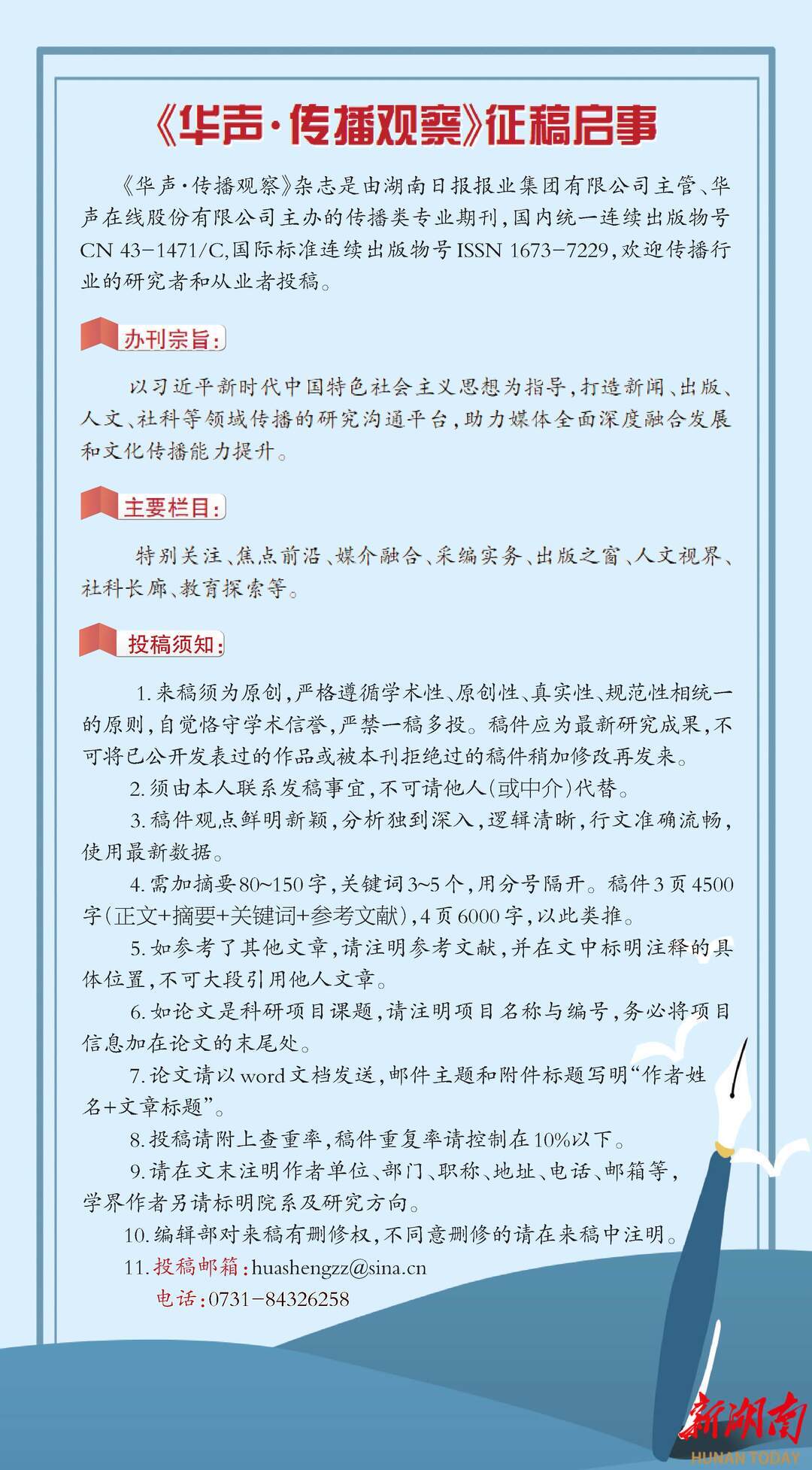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