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21 08:1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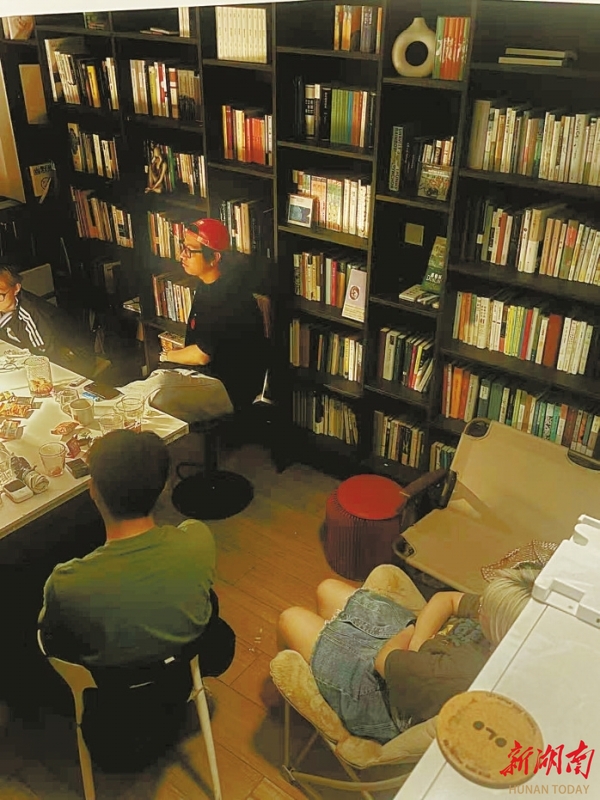
廖慧文
读书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在教育匮乏的时代,读书会是学校“替代品”;当大众教育逐渐普及之后,读书会走向了社区和社会,成为人们学习、交往和休闲娱乐的选择。即便在社交方式和阅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互联网时代,不少人依然热衷于围绕着书籍展开讨论。他们交流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体验、困惑和分歧,还感受着与他人的连接。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前夕,我们走进读书会。
共振空间
这晚的主题是“离去与坚守”。在长沙向东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参加21瓦青年社读书会的7人依次介绍手中的书。
一位男生举起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短篇小说集《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介绍其中的一篇——《黑暗茫茫》。麦克劳德笔下的乡村大多与煤矿有关,人们努力生活,却总因为工作而与伤痕打交道。“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年轻人的离开与怀念,老年人的坚守与孤独。”他说。另一位姑娘接过话头,推荐的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把话题引申至稳定与自由的关系。
依次发言。有人推荐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认为商鞅的改革亦是一种坚守;有人提及《曾国藩传》,感慨一个人生命中就要经历很多次离去与坚守。话题发散得很广,简要介绍书籍内容、个人感悟,最后收拢到主题上来。
“离去有时候就是为了坚守自我、走向自我。”有人讲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著名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有人反驳,“这只是一种不负责任。”一群人热火朝天地争论。
主理人唐浒负责控场,偶尔提醒时间。在这半年里,唐浒一直过着“双城生活”。每周二、周三晚上,他分别在老家株洲和长沙主持一场读书会。活动通常在8人左右,主题提早一周在微信群里由书友们商量着定下。感兴趣的人,便在群内接龙报名,带上一本与主题相关的书籍参与。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临时赶来“体验一下”。唐浒是“80后”,曾在广东一家知名媒体供职,后来在一家新创立的公司工作。一场工作酒局过后的早晨,他在镜子前审视自己委顿的神情,“很油腻,我不想再这样”,于是离职回湖南生活,在业余开办读书会“寻找自己的精神空间,恢复生命的完整”。他有十余年组织社群的经验,想把社区建设与读书会、观影会等青年活动相结合。
半年前,他与向东南社区合作。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并提供一些补助。社区图书角里有一些书友共享的图书。我翻开旅行作家刘子超新作《血与蜜之地》,一张手写便条贴在扉页:“远方不应是一种诗意化的陈词滥调,它指向这片土地生长起来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
这晚活动结束后,仍有人留下来交流。长沙小伙李正杰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只要有时间都会到场。他也参加其他读书会,享受在实体空间交流的快感。虽然是长沙人,但他从外地读书、工作回来后,曾长期找不着归属感。“有一次我在阿克梅书店和书友们一起读诗,忽然就感受到了一种地方上的情感,一种乡愁。”他依赖这种情感力量的共振。
社区的补助期只有半年,眼看着就要结束。近期,唐浒将一次读书会改为交流会,请书友们提些建议,探索可持续的低成本运营模式,大家一直聊到了深夜。
智识生活
“我们挑选了10本作为2025年的共读书目。不限定类别,依然是缓慢地每个月读一本。我们希望这些书能帮助你思考文化当中荒芜的部分,找到那些被削弱的、退回乃至沉默与消逝的东西,以及敲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窄门。”一个月办一场共读会,是身处长沙河西大学城的回望书店从开店之初就坚持的事。今年初,书店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宣布了每个月的共读书目。3月,按惯例是女性主义,今年选了《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4月,是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心灵生活》;5月,是艺术史家巫鸿的《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讨论什么是传统中国绘画……书目涵盖政治、哲学、艺术、心理学、社会学等。
读书经常是一件孤独的事。普鲁斯特曾说:“读书时,我们每个人在接受他人思想交流的同时仍然保留孤独,即继续享受我们在孤独中享有的智性力量。”在孤独的阅读之后,交流的渴望也在滋生。
“我太爱这件事了,”店主前驰语调欢快:“我希望把共读会永远办下去。”她保持着一个月读4本书的频率,认为读书应该读得更精细一点儿。书店有个30来人的微信群,里面都是阅读面很广的书友,有教师、编辑、高校学生,由他们来推荐共读书目,再由前驰选出。“我尽量选不同类型的、自己没有读过的、不是非常流行的书。”共读会向参与者提出要求:参与之前,要基本把书读完;阅读书籍本身,而不是先阅读他人的评论。
他们共享着一种智识生活。不少书友会把看不懂的地方折了页,在共读会上讨论。“有些书是有难度的。离开校园,有了疑问又不能去问老师,而且老师也是有专业限制的。但是有了共读会,平时觉得不敢看的书就敢看了,因为知道到时候有人会一起探讨,这可能就是共读会的意义。”前驰说。
一场活动的线下参与者通常在15人左右,一半是固定书友。他们把共读当作推动自己求知的力量。前驰对一位高中生印象尤其深刻,“他关心很多社会议题,比如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可能要进入社会有了阅历才会关注到这些议题,而他非常敏锐。我觉得这是阅读带给他的敏锐。”
我请前驰总结共读会书友们的特征。“爱,思考,行动。”她没有犹豫,“阅读也是一种行动。”
推荐者会成为该期领读人,负责引导讨论,而每个人方法都不同。下一期的领读人学哲学专业,“他领读的方式是一直抛出问题,很有自己的风格。你来旁听呀!”
社交之岛
云起读书会在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loft公寓里。两面墙放置落地书架,中间放一张大桌子,依着落地窗。厨房设置成水吧,有饮料和零食,还可以自助调酒,落座需要均摊一点饮料费。主理人思思原本在市中心的商场里开一家百来平方米的书店。这是她的副业,但一个月两万元的亏损,让书店难以为继。关店后,她转而租了这间小公寓作为书房,也作为读书会的场地。
“现在只当为自己的爱好消费啦!没想过要挣钱。”思思说,她始终还是喜欢有书和书友陪伴的生活。书架上的书很新,哲学、艺术、文学理论、人类学,都是她细细挑出来的。“欢迎来看、来借。”
思思喜欢《老友记》。这部已经在全球火了30年的美国电视剧聚焦青年友谊,剧中6个性格、背景各不相同的人,组成了一段积极和谐的生活体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刘擎曾建议用一种“关系型个人主义”来克服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危机。思思觉得,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友谊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它可以抵御这种危机。“人应该有五六个亲密好友”,深受友谊滋养的她很想推广这种社交模式,于是把每场读书会都设为“六人局”。书籍是连接点,大家往往从书籍里的议题出发,谈论自身、阐述观点,也激烈辩论。歧见与共识在不断循环。
快节奏的生活、信息的过量接收,让现代人普遍处于社交倦怠之中。但人与人的社交需求依旧广泛存在。“线上社交的人们无法清晰地彼此‘看见’,线下社交是不可替代的。”思思说,“六个人,就组成了一座社交之岛,你可以在这个岛上玩,有时候又跳到新的岛上去。而哪个岛是你最喜欢的?你逐渐可以筛选出‘同频的朋友’。”
元气读书会主理人有两位,袁理曾是媒体人,表达能力强;宋秋平在广告公司工作,她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阅读面广。这一夜,袁理领读陶渊明的诗歌,形式有点像文学通识课课堂。她介绍陶渊明的生平与创作,引用美学鉴赏家顾随的赏析。书友们再依次读一首陶诗,讲讲自己的感受。
读书会的受众年龄跨度很大,不少书友参加工作多年,甚至已经退休。“我们面向普通大众,阅读门槛要低一点。”读书会也是她俩的副业,每周一场收费、一场免费,偶尔也为企业定制读书会活动,就这么支撑了下来。“为什么读这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和生平?我们希望大家从中看到人的生活、思考人的境遇。前人走过的路会给后人启示。”袁理说,有位书友一直在医院照顾久病的亲人,但几乎每周都来参加读书会。她不太发表观点,只静静地听,会后和大家轻松地寒暄几句。“我们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社会,各种事务缠身,可是有这么一个空间和时间,我们来读读书、讨论一些和日常生活工作无关的话题。哪怕是人际弱连接,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
“有书友说我们是‘回望药店’。”前驰笑着说,有时候结束一场讨论,书友们觉得接受了一场“群体心理治疗”,感到被他人所理解、包容和安慰。
谈话通常很热烈,书友们你来我往地递着话题,织起了重重叠叠的网络。友谊在此诞生,共同体在此孕育。其中许多书友都自认“社恐”,但在这样的场景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排斥社交,而只是想要更为舒服的社交,“因为,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
责编:黄煌
一审:黄煌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